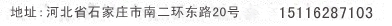许云和ldquo富艳rdquo的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宋摹本
“富艳”的史学和文学批评意义
许云和
内容提要富艳是魏晋南北朝史学和文学批评中出现的一个重要批评术语,关于其内涵,后来论者一般多是从作品风格或词采的层面进行认识,这并不符合原意。在当时的语境中,富为一义,艳则为另一义。就史学著述而言,富是褒扬史家史才即叙事能力达到的高度;就文学创作而言,富是赞扬作家文才即写作能力达到的高度。艳则为“文辞可美之称”。在当时的史学和文学批评中,号为富艳者唯左丘明、陈寿、曹植、谢灵运数人,足见它是被视为史才和文才的最高表现,已成为衡定作家才华和水平的最高标志。谢灵运评曹植才八斗,自许一斗,自也是隐含了文才表现达到极致的意思,与世所称曹植、谢灵运文才富艳的内涵完全一致。富艳后来淡出史学批评以及在文学批评中原始语义偏移,一是与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对词义的选择性注意有关,二是其义渺焉难详,论者不知是从孔子“儒行”说中移植过来的概念。
关键词?富艳;史才;文才;八斗;儒行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和文学批评中,曾经出现了一个重要批评术语,即“富艳”。史家唯左丘明和陈寿当之;文学家当之者则唯曹植、谢灵运和晋徐藻妻陈氏《与妹刘氏书》言及的元方、伟方,可见获得这个评价的人并不多。元方、伟方在文学史上其名不彰,陈氏以富艳称之,显是出于亲属间的客套。然左丘明、陈寿、曹植和谢灵运则不同,他们都是震铄古今的史学或文学巨匠,时论以富艳称之,自应是从其作品实际成就和水平出发而得出的比较严肃的结论。富艳只授史学和文学巨匠,规格不可谓不高,但于其批评内涵,后世论者却少作深究。一般多认为是专指作品词采风格,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回到历史语境中对富艳一词的来源、运用情况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包含更多史学和文学批评的意义。从创作上讲,它是史家史才和文学家文才的最高表现;从批评角度来说,它是史学和文学批评所树立的一个衡定作家水平和成就的最高标志。至于富艳专指词采,那是后起的观念。考察富艳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和文学批评中的含义,对于深入认识这些史学和文学大家的才华表现和创作成就以及时人的史学和文学批评理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富艳:以史才为核心的史学批评
富艳一词,最早为史学批评所用。东晋常璩评价陈寿的史学成就,谓其“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1];而同时的范宁也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2]很显然,作为史家一生著述成就的总结,这里用富艳一词进行赅括,就决不是单一从词采层面出发,而应包含更多方面的义指。情况也确乎如此,范宁言《左传》“艳而富”“富而不巫”,已将两个字分而言之。唐代杨士勋疏范宁之言时也充分领会到这一点,以富为“属辞比事,有可依据”,艳为“文辞可美之称”[3]。其实,《左传》号为富艳,是当时学界的共识。他们在评价时虽没有直接使用富艳二字,但其内涵完全一致。如王接言“左氏辞义赡富”[4],“辞赡”表其艳,“义富”则著其富。贺循也说《左传》“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5],前句拟其艳,后句则拟其富。这就表明,《左传》的富艳,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义含两端,而非一事。
《乾隆御定石经·左传》,清乾隆间内府亮墨拓本
实际上,范宁评《左传》为富艳,是渊源有自的,按杨士勋所言,富艳最早在扬雄《法言》中是表述为“品藻”的,二者同义。《法言》云:“左氏,曰品藻。”[6]司马光注:“品第善恶,藻饰其事。”[7]“品第”与“藻饰”,一为叙事,一为文采。可见,范宁富艳说实本扬子“品藻”而来,具体而言,富乃“品”之义,艳则“藻”之义。
至于常璩评《三国志》富艳,虽没作具体阐发,但他又说:“吴平后……又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8]前言《三国志》富艳,此又言其“品藻”,足见其观念中,富艳与品藻同义,同样是表达了富和艳两个义指。《三国志》号为富艳,当然也非常璩独见,当时不少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裴松之云:“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9]崔浩亦云:“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10]又《晋书》评陈寿云:“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1]所言正与杨士勋所释《左传》之富含义相同,皆就其叙事而论之,而艳则为另一事。这种意见的相同表明,诸家赞扬的就是《三国志》的富艳,而表达的义指也仍然在于富和艳两个方面。
那么,富艳在史学批评中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按杨士勋所解,《左传》的富,主要体现在“属辞比事,有可依据”,孔颖达疏:“《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12]据此,则“属”和“比”就是一种历史叙事的行为,具体指《左传》能够把历史上诸侯朝聘会同的相接之辞、褒贬之事按一定的思想和方式重新组合排比出来。“有可依据”即确切可据,言其叙事有其历史确切性。可见,《左传》之富不是满足于原有史料的丰富或翔实,而是通过重新组合排比史实来书写历史,使历史获得新的生命,赋予它一种新的历史确切性。《左传》这种历史编撰方法,获得了后人高度认可。卢植云:“邱明之传,本末《春秋》,博物尽变,囊括古今,苞裹人事。”[13]表彰的就是左丘明能够在《春秋》原有框架和材料基础上,以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去触摸历史发展的脉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因《左传》的历史编撰表现出这样鲜明的特征,所以人们历来是不把它单纯地看作注疏意义上的传,而是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王接就说《左传》“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14],认为《左传》由传统经注的义理阐释走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成为富有独立思想和创新意识的史学巨著,在《春秋》之外别是一家。高佑更指出:“至若左氏,属词比事,两致并书,可谓存史意,而非全史体。”[15]意思是左丘明的史学成就还不仅仅在于从注疏走向史体,更重要的是能够独出机杼,自铸伟词,以自己的思想和心灵书写对历史的感受和理解。由此可见,《左传》的“属辞比事,有可依据”,包蕴了丰富的历史书写意义,表达了一种先进的历史书写观念,它要求史家用思想和灵魂来书写历史,形成新的信史,而不是仅限于纯客观地呈现历史,这就是《左传》的书写之所以为富的重要内涵。至于《左传》之艳,则主要指其“文辞可美”,也即司马光所言“藻饰其事”。这一点,也同样是时人的共识,如王接言其“辞义赡富”,荀崧言其“多膏腴美辞”[16],皆是艳的另一种表达。
“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则是《三国志》富的义指所在,前者指对史实的解说、评议多有可取;后者指对史实的把握精审准确,义颇同《左传》的“属辞比事,有可依据”,说明论者也同样认为陈寿是用思想和灵魂来编撰历史,筑成确切可据的信史。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后来一些史家的认同。《三国志》写成后,范頵作推荐时即赞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17],认为陈寿并非是纯客观地呈现史实,而是对历史事件渗入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有其作史“奸慝惩戒”[18]的责任和担当。而李慈铭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陈寿这种富有历史批判意识的良史精神:“承祚身仕晋武之世……其书盛行,乃悉归刊削,绝不顾及,此所以为良史也。”[19]吉川忠夫更从陈寿所处的时代和遭际出发,揭示了他在书写这段历史时独特的心理和思考,说陈寿有“洞穿历史的冷彻的眼睛”,即是言其富有卓越的史才和史识,有他人所不具的独特经历和感受,以一个亡国者的历史审视和心灵思考完成了这部巨著[20]。由此看来,和《左传》一样,《三国志》的“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同样是在拥有可信材料的基础上致力于一种历史的思考和判断,把历史过程化为思想过程,用自己卓越的历史意识和创造力使“自然的过去”成为“活着的过去”[21],使史书的书写呈现出一种创造性形态而非文献纠合式的复制形态。至于《三国志》的艳,其义也是文辞之美,《晋书》即言“陈寿含章,岩岩孤峙”[22],刘勰也称在诸多三国史书中,“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23],皆认为其词采独树一帜。
综上言之,历史著作之富乃是就史家历史解释和历史叙事达到的水平高度而言。它要求史家不把历史过程视为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思想过程,即用思想和灵魂来过滤那些单纯的事件序列,批判旧的历史知识,重新书写自己理解、认识的历史,把一个“某种给定的观念世界改造成为一个远比一个世界更多的世界”[24]。这种历史叙事的先进性和创造性,就是富的本质和内涵所在,而它恰恰就是刘知几所说的一个史学家“史才”的最高表现,强调的是历史编撰不能因循守旧,应发扬创造精神,以重构的思维来编撰历史,使过去的历史知识获得增值,不能“有学而无才”[25]。而历史著作的艳,则是指其文字表达上呈现的华美之感。《左传》《三国志》的富艳,充分体现了左丘明、陈寿无与伦比的史才和杰出的语言表现能力,他们以此建立的一代史学经典,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引领着历史编撰的方向。即此而言,富艳树立的就是一个极高的评价标准,它衡定的对象都是超一流史家的历史撰述。
二富艳:以文才为核心的文学批评
那么,这一时期富艳运用于文学批评,其义指是否也与其史学批评的意义相同呢?先看晋徐藻妻陈氏《与妹刘氏书》的一段文字:
元方、伟方并年少而有盛才,文辞富艳,冠于此世……先君既体弘仁义,又动则圣检,奉亲极孝,事君尽忠,行己也恭,养民也惠,可谓立德立功,示民轨仪者也。但道长祚短,时乏识真,荣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标方外迹也。老庄者,绝圣弃智,浑齐万物,等贵贱,忘哀乐,非经典所贵,非名敎所取,何必辄引以为喻邪!可共详之。[26]
需要指出的是,此所言“文辞”,并非指辞藻,而是指文章。所以,陈氏赞扬元方、伟方“文辞富艳”,就并不只是着眼于其词采,而是对其创作水平的一个总体评价;谓其“有盛才,文辞富艳”,即是赞其文章体现了极高的文才,达到了富艳的高度。而陈氏指出伟方以老庄思想拟喻其先君行为事迹,则是批评他为文富而巫,不得其实,因其先君是“体弘仁义,又动则圣检”的儒者,“本不标方外迹”。这个批评,正与范宁“富而巫”相同,已是将富这一义项从富艳中单独提出,别而论之。表明在时人的观念中,富艳实际所指,同史学批评一样,也兼具两方面的内涵。
再来看看这个时期其作品被论家许为富艳的曹植和谢灵运的情况。陈寿评曹植云:“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27]文才指文学的写作才能,“文才富艳”是说曹植写作才能极强,达到了富艳的高度。这也不是一般性地夸赞其词采水平,而是就其整体的写作能力而言,兼及了富和艳。陈寿的赅括,虽没有具体阐发其富为何,其艳为何,但从后人的评价可以体味出,他们对曹植作品的评价,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是在陈寿指出的富艳这一义域中进行。比如《诗品》对曹植的评价[28],就是其例。所谓“词彩华茂”“体被文质”,说的就是曹植诗的艳,谓其得文质相兼之极。实际上,曹植诗的艳,早先即为人注目,鱼豢云:“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29]左思《魏都赋》也言其“摛翰则华纵春葩”,给予高度评价。说明锺嵘的看法,是建立在群体认识的基础上的。而“骨气奇高”、“情兼雅怨”、“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云云,则是从文章写作的各个方面来说曹植诗的富。一言其情具《国风》之雅、《小雅》之怨,二言其志如周孔,三言其姿比龙凤,四言其音似琴笙,五言其文若黼黻[30]。即曹植诗在情志、风采、声音、词采等方面的表现都是时之冠冕,以巨大的知识才华奉献了诸多富有创造性的写作模式,让后来者取资无穷。曹植诗的富艳,萧绎也有过相同的看法,所谓“辞致侧密”说的是其艳,“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则谓其富[31],着眼的是其非凡的文学表现能力。这方面,后来论者也多有体会,沈德潜云曹植诗“但实事贵用之使活,熟语贵用之使新,语如已出,无斧凿痕,斯不受古人束缚。”[32]丁晏也认为曹植诗“根乎学问,本乎性情”[33],一方面是学之富,一方面是才之富,是以才华驱使性情和学问的结果。沈德潜、丁晏从作品阅读中获得的这些认识,是可以在《三国志》曹植本传中得到印证的,本传言其“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34],说明他“善属文”的确有一个广博的知识基础。正因有学问的底气和丰沛的才气,他才树立了“与《雅》《颂》争流”[35]的崇高述作理想,希望创作出磅礴大气、文质彬彬的君子之作,而这其实就是一个富艳的标准。
《曹子建集》,明万历刻本
钟嵘言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意思也与陈寿评曹植相同。才高言其富,谓其有强大的写作能力;词盛说的则是艳,即《晋书》所谓“文藻艳逸”[36]。那么,谢诗之富艳具体又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诗品》对谢诗的评介[37],即是对谢诗富艳的一个具体诠释。所谓“其源出于陈思”,是说谢诗得曹植之“词彩华茂”,表现出艳的一面。而“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是说谢灵运为了文学形象的塑造,特别注重诗艺的探索和追求,以新的文学语言创造出诸多新的文学形象。这一点,后来论者表示了高度的认同,如沈德潜说谢诗“大约经营惨淡,钩深索隐,而一归自然,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38],认为谢灵运能够突破旧的语言形式,在塑造文学形象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而黄侃对谢灵运在诗歌语言方面的求新求变更有深入理解:“世人好称汉魏。而以颜谢为繁巧,不悟规摹古调,必须振以新词;若虚响盈篇,徒生厌倦,其为蔽害,与剿袭玄语者政复不殊。以此知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矣。”[39]充分肯定谢灵运打破旧传统,在文学语言上“振以新词”的贡献。而“若人学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云云,说的则是谢诗的富在于哪些方面。“学多才博”,即《宋书》本传“少好学,博览群书”[40]之谓,言其有丰富的知识储备,由此造就了谢灵运的才博,因其才博,故而在创作时能够自如地运用《易》《老》《庄》入诗,造其语而化其境,给人一种内无乏思的感觉。由于有广博的知识学问,谢诗描写客观景物往往能做到即目则书,仿佛天地间任何事物都可以尽收笔底,白居易言谢诗“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41],就是对此最好的概括。谢灵运自己也说过:“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42]说明他很懂得“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43]的道理,通过知识的学习积累来增长自己的才华。唯有读书多,写作时才能得心应手,心领而神会。
总而言之,文学作品的富艳,衡量的是作家写作能力所达到的水平高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由于作家积学深厚,文才巨大,具备高超的表现能力,所以创作时往往能以非凡的文学手段驱使其广博深厚的知识学问,语语求新,字字避熟,将普通语言疏离或陌生化,使其被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44],形成新的文学语汇,以突出描写对象,获得新奇的艺术效果。通过这个创造性的过程,形成新的文学意境和形象,将一个全新的知识和思想世界展现在人们眼前。作家的这种文学写作能力,世人尝称之为文才,且与富艳二字形成固定搭配,表示的意思非常清楚,即富艳是作家文才的最高表现。陈氏谓元方、伟方“有盛才,文辞富艳”,陈寿云“陈思文才富艳”,锺嵘言谢灵运“才高词赡,富艳难踪”,都表明二者存在的这一关系。而按照时人的标准,文才表现能达到富艳这一境界的文学家,就只有曹植和谢灵运,他们是那个时代才华最为杰出的文学家,其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表现和成就,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以一种极大的影响力而自通于后叶,昭示着未来文学发展的方向。
三富艳之失:史才与文才的负面效应
虽说富艳是史家和文学家创作才华的高度体现,但是,为文臻至富艳的境界,却难免不有富艳之失。
《左传》的富艳,世所公认,但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作为杰出的史学著作,也因其富艳而带来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范宁所说的“其失也巫”。杨士勋就指出《左传》之巫体现在“多叙鬼神之事”[45],汪中更将巫概括为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五事[46]。杨士勋、汪中指出的“巫”,记录的都是与鬼神迷信相关的活动,与作为记录人类社会活动内容的历史编撰要求相悖,不符合那个时代历史编撰专于人事的理念,故而指其为“巫”。然而范宁只是从历史编撰角度解释这一情况,并没有深入挖掘《左传》巫的历史原因。实际上,《左传》的巫,与春秋时代巫史同职有着密切关系,皮锡瑞就指出左丘明是身兼巫史[47],既处于巫史同职的时代,他在历史思想和观念上就不免会有那个时代打下的烙印,难以跳出神权史学和神话[48]的圈子,所以他驰骋所学,蔓衍其词,以怪力乱神入史,也就是必然。左氏涉于巫,在巫史同职的时代当然是不以为怪的,但到了巫史分职、历史编撰专于人事的年代,其居巫职而记录的那些鬼神之事,后来论者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观照,自然也就会被视之为为才所累,在不该发挥才华的地方发挥了自己的才华,为此而诟病不已,认为左氏才华虽大,但却是肆意骋才,使得《左传》叙事不知检括,破坏了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从根本上讲,《左传》的巫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客观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不能全归于左丘明的刻意骋才。
《三国志》的富艳之失,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后人诟病的曲笔粉饰。刘知几就曾批评过陈寿对当权者曹操、司马懿的回护[49]。赵翼《廿二史札记》曾专设“三国志多回护”一条,批评《三国志》“回护过甚”[50]。不过,赵翼虽然对《三国志》的曲笔回护极其不满,但他同时也注意到陈寿的回护是特殊历史时期政治高压下的一种权宜变通行为,有不得已的苦衷,因此给了他一种同情之理解[51]。如此说来,《三国志》的富艳之失,同样也不能归为陈寿历史书写本身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局限使然。不过,关于《三国志》的回护,也还要注意到时人的看法,《晋书》即言王沈尝“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52],认为相对于同时的三国史书,陈寿在这方面是做得最好的。表明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已尽到最大的努力,情形并无如此不堪。
陈寿《三国志》,清光绪二十年岭南培远堂刻本
据陈氏《与妹刘氏书》,可知言不符实、偏离创作客体实际而肆意发挥是文学创作富艳之失的一个突出表现。曹植作品的富艳之失,实际上也在于这一个环节上。比如其《汉二祖优劣论》对两汉文臣武将的评价,诸葛亮就觉得很不得体,认为光武麾下的文臣武将并不逊色于高祖手下的韩信、周勃等人,曹植的评价有违历史实际[53]。而刘勰纵论古今文章得失,也指出曹植作品有很多这样的毛病。比如其《文帝诔》,刘勰批评说:“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旨言自陈,其乖甚矣。”[54]刘勰认为《文帝诔》违反了诔的体制要求:一是失之简要,流于繁缓;二是结尾置所诔对象于不顾而自抒情志,行文脱轨,放荡不拘。而在《指瑕篇》中,刘勰则指责了曹植《武帝诔》《明帝颂》的用词不当:“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55]在《事类篇》中,又批评其《报孔璋书》“滥侈葛天,推三成万,信赋妄书”[56]。在《封禅篇》中,刘勰又针对其《魏德论》,指出其玩弄才气而自损文气的毛病:“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勣寡,飈燄缺焉。”[57]封禅一体,贵在“经道纬德,以勒皇迹”[58],而《魏德论》驰骋千言,文气十足,却是“劳深勣寡,飈燄缺焉”,迂缓有余而气势不足。凡此种种,皆是属于才多而不知检逸,失去为文法度的制约所致。
谢灵运的富艳之失,与曹植是惊人的相似。钟嵘指其“逸荡”“颇以繁芜为累”[59]。萧纲亦批评其“时有不拘”[60],为此,他还专门作《谢客文泾渭》三卷[61],掎摭其利病。齐高帝也说“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62]。这些,正是刘勰所揭示的曹植诗的通病。具体就是指谢灵运的创作因才华太大,过于用才而不知收束,使得造词造句出现了难以容忍的毛病,诸如:因语语求新,字字避熟,语言修饰过度,词句让人顿感生涩;追求句意的新颖,思想放飞过甚,让人不知其意有首尾。正因谢诗的弊端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影响,萧子显才格外重视,对学谢者发出了警告:“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63]萧氏希望学者能够正视谢诗存在的问题,不能盲目崇拜,率意模仿。谢诗的这种毛病,后人也多所不满,贺贻孙就说“谢诗虽多佳句,然自首至尾,讽之未免痴重伤气”[64],姚范也说谢诗“颇多六代强造之句,其音响泎涩”。[65]谢诗的问题,显然不是困于才短,而是困于才多所致,才多而致累,大概是天才文学家难逃的宿命。
综上所言,左丘明和陈寿的富艳之失,并非历史书写上的为才所累而致,它基本上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对此必须给予同情之理解,仅仅站在文章表达角度来苛责其失是不合适的。曹植与谢灵运则有不同,他们以极大的才华致力于文学创作,在艰辛探索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富艳之失,虽然也有历史局限的因素,但基本上可归为文学创作上的一种才多之患。不过,对于二人的富艳之失,还必须要看到的是,有的地方固属作者自己的原因,但一些论者看到的所谓失,却是自身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的问题。理由是,曹植和谢灵运在创作上所发挥的极大创造力,必然使其作品产生较大的疏离,仿佛日常生活世界突然被陌生化,当它以一种新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时,肯定会使一些固陋俚塞、见识有限的论者顿感不适。因长期停留于旧的诗歌思维模式,来不及反应,就会觉得作品语言或所写形象在观瞻和理解上隔碍甚多,觉着不合情理,于是就视之为有毛病。比如潘德舆说谢诗“用事抒词,凑补支绌,乃儿童装字为诗者”[66];吴淇说谢诗“语多生撰”[67],所言即有似于此者。但是,在一些识力卓绝的论者眼里,却并非如此,它们往往会被视为充满创造力的文学表现而备受称道。曹植和谢灵运的一些作品在批评史上之所以常常充满了正反两方面的争议,原因正在于此。
四八斗、一斗之喻与富艳、文才之关系
因富艳与文才存在着密切关系,而整个魏晋南北朝的著名文学家中,论者许为富艳的只有曹植和谢灵运,这就让人不能不想到文学史上一段著名佳话,这就是谢灵运评曹植才八斗,自许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谢灵运的评价,同样也是从文才角度来推许自己和曹植,其选择的对象和评价出发点居然与时议如此相同,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呢?
以往,学界之所以对此语津津乐道,主要是它表现了一个天才文人俾睨天下的自负和狂傲,可以资谈笑,满足人们的膜拜之情。但是,了解陈寿、钟嵘对曹植和谢灵运的认识和评价后再来回味谢氏之言,就会觉得此语决不仅仅是可资谈笑那样简单。实际上,这种惊人的相同本身就意味着,谢氏发为此言,与其说是为着一种性情上的宣泄,倒不如说是为着一种文学批评意见的表达。
然而,话虽如此,谢灵运此言却存在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它虽然为学者乐于引述,但其来源出处为何?是否出于谢灵运之口?一直以来鲜有稽考其实者。因此,讨论这句话所包蕴的文学批评内涵以及它与时议的关系,就有必要先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实际的考察。
考谢灵运此言,最早见于李瀚所著《蒙求集》,宋徐子光注引旧注曰:
旧注引谢灵运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继之。[68]
《蒙求集》曾一度被误为唐末后晋李瀚所作。然据余嘉锡、郑阿财、朱凤玉考证,《蒙求集》成于天宝五载之前,作者为唐代宗时翰林学士李翰[69]。按李良《荐蒙求表》,云李瀚“撰古人状迹,编成音韵,属对类事,无非典实,名曰《蒙求》,约三千言。注下转相敷演,向万馀事”[70],则知徐子光注引旧注,实为李瀚的随文自注,此与《佚存丛书》本《蒙求集》题“唐安平李瀚撰注”相合。如此,则李瀚引谢灵运语在天宝之前就已存在。而复据李华《蒙求序》“随而释之,比其终始,则经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71]及李良《荐蒙求表》“错综经史,随便训释”之言,又知李瀚引注文献均是出自当时尚存的前代经史百家之书,说明谢氏此言并非来自社会上的口头流传,而是史有明文。那么,李瀚所引究竟是出于哪一类旧籍呢?从这句话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来看,它应出于唐代尚存的六朝史籍或文学批评著作中。今天我们固不能从现存六朝旧籍中求得这句话的具体出处,但需要注意的是,唐代所存六朝旧籍,多有今不能见者,就刘宋一代之史而言,据《旧唐书·经籍志》,唐代除沈约《宋书》一百卷外,尚有徐爰《宋书》四十二卷、孙严《宋书》四十六卷存世。谢灵运一代名流,这些史书自然少不了为其立传,其中应有沈约书所不载者。就文学批评著作而言,据《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可知刘宋及其以后除《文心雕龙》《诗品》外,尚有谢混《文章流别本》十二卷、孔宁《续文章流别》三卷、傅亮《续文章志》二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等。这些文学批评著作,多有作家传记材料存焉,其中也应有刘勰、钟嵘书所不载者。这些唐代尚存的六朝史籍和文学批评文献,正可为李瀚撰《蒙求》所取资。
再从这句话本身来看,也非常符合谢灵运狂傲的个性。《宋书》本传就曾言其“好臧否人物”[72],并不知有忌讳,这方面的个案,《宋书》记载不少,如他折辱孟顗云:“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73]他也好批评作家作品,如《诗品》就有“谢康乐常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74],“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尔”[75]。可见谢氏确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他能说出“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的话,并不奇怪。
明仇英《谢灵运烹茶行乐图》,绢本
此语既符合谢灵运狂傲猖獗的个性,且是李瀚得之于六朝旧籍中,就难以否定其作为历史文献的确切性。明确这一点,也就可以继续讨论上面提出的问题了。
那么,谢灵运的话究竟包蕴了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内涵呢?细味不难看出,在貌似狂言的背后,是他总结一代文学发展强烈的文学史意识,旨在对曹植和自己的文学才华、成就、地位作一个历史性的评估和定位。一方面是说,曹植和他是才华最大的作家,其他人不过是众星拱月而已;另一方面则是说,曹植是笼罩整个魏晋刘宋文学的人物,在史上才华最大,成就最高,是无法超越的泰山北斗,自己虽然文才盖世,但比起他来还是有八斗与一斗的距离。可见谢灵运虽然狂傲,但对曹植却是真心服膺。谢灵运这样来衡定曹植和自己的才华,其理由又是什么呢?其实陈寿和钟嵘之评已给出答案。陈寿说曹植“文才富艳”,钟嵘说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已表明富艳是一个作家文才的最高表现,所以谢灵运在文才方面强调曹植独得八斗、自得一斗,自也就是强调其写作能力的强大,而能够对此作出恰当的赅括的,当然莫过于富艳一词。可见,文章的富艳就是谢灵运发为此言的根本依据。所以谢灵运强调曹植和自己才高,陈寿、钟嵘说曹植和谢灵运富艳,就是一个意思,说明二者认识完全一致,都是认为曹植和谢灵运是那一个时期才华最大的作家,其才华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到达了富艳这一最高境界。据此而言,谢灵运的八斗、一斗之喻,就是一种充满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具有严肃的批评内涵,并不可以一般狂言视之。
谢灵运这样来总结曹植和自己的文学表现和成就,将其论定为那个时代才华最大、成就最高的两个大文学家,并非偶然,它不只是与陈寿、钟嵘的意见相合,更与当时文学批评大背景下社会的集体认识密切相关。
自古谈文学史,就有“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76]的心理,一个时代的杰出人才,往往会招徕世人的围观和仰望,而曹植和谢灵运就是这样的人物。曹植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当时陈琳就有一个崇高评价和定位:“君侯体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拂钟无声,应机立断,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77]杨修也盛称其文“虽讽《雅》《颂》,不复过此”,“仲尼日月,无得逾焉”[78]。这虽然是人臣的一种极力吹捧,但他们认定曹植就是仲尼日月,却具有相当的学术眼光,为后来曹植地位的定位定下了基调。而自此以后,曹植在文学史上的至高地位,更是谈家口实,标榜不绝。比如钟嵘就是这样来论定曹植诗的文学地位:“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79]而且,钟嵘还说:“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80]这个定位,与谢灵运的八斗、一斗之喻如出一辙。萧绎也说曹植“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同样将曹植定位为诗人中的儒者巨子。而刘勰也一再表彰,言其为“群才之英也”(《比兴》)。可见曹植为建安以来的第一诗人,那时已有论定,谢灵运推许曹植为八斗才,其内涵与其前后论者的看法是基本相合的。
至于谢灵运,其文学地位当时也有一个论定。一是议者将其与颜延之并提,认为二人是刘宋时代最大的文学家。如《南史·颜延之传》云:“是时议者以延之、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81]《南史·谢灵运传》也称灵运“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82]。二是议者认为谢灵运的文学成就为江左第一。《宋书·谢灵运传》言其“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南史·谢灵运传论》亦云:“灵运才名,江左独振。”[83]值得注意的是,议者为颜延之的文学地位定位时,至多是说他和灵运并称江左第一,并没有单独说过他是当世第一,表明在时议的天枰中,人们还是倾向以谢灵运为当世第一。有趣的是,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84]这就透露了一个信息,虽然议者并称颜谢,但在颜谢之间,却有一番孰为天下第一的争斗,延之自负才气,自是不甘居于灵运之后,故而才去问鲍照,请其裁决。谢灵运对他们二人孰为第一的态度和反应虽不见载诸史,然而可想而知,以谢氏之心高气傲,更是不会把颜延之放在眼里。所以谢氏自言我得一斗,恐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议者的一种回应。也许是谢灵运这一自评合乎时议的天枰,对后来议者造成了极大影响,自此以后,人们对二人文学地位的看法确实有了改变,一般都认为,谢灵运是江左最大的文学家,而延之声名由是寖焉,《诗品》“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85]的定位,就已反映了这一情况,而这正与谢灵运对自己的定位相合。
由此可见,那个时代人们对曹植、谢灵运文学成就和地位的论定,已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种论定同样也是以曹植、谢灵运的文才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为依据。谢灵运的八斗和一斗之喻,其批评内涵与之完全相合,表明谢灵运与其他批评家是持有一个共同的批评原则和标准。
《谢康乐集》,明万历十一年南城翁少麓刻本
五富艳的语义退隐与偏移
富艳的含义已如上述,然自唐以还,富艳几乎淡出了史学批评,人们很少用它来评价史学著述,即在文学批评中,富艳的原始语义也是称指范围缩小,其义变成专指作品风格或词采上的“美盛、华丽”。后来的历史文献显示,富和艳早先本是一个并列词组,后来则变为一个偏正词组,富成了修饰艳的程度副词,意为非常、十分,与富丽一词的含义非常接近。如《旧唐书·吕温传》称“温文体富艳”[86],就是从文体即文章体貌特征的角度来说的,已失范宁《左传》富艳的原旨。皮日休《桃花赋序》谓宋广平《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87],此富艳,则是专就宋广平这篇赋风格的轻艳来讲的。而《旧唐书·白居易传》言“居易文辞富艳”[88],此则专指白氏词采上的“美盛、华丽”。宋以后,富艳义指也同样是沿袭唐代,如陈振孙说周邦彦“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89],此即赞扬周邦彦词辞藻的华丽。富艳在宋人观念中的含义,朱胜非曾作了一个形象的诠释:“徐雅中、李九皋俱善诗,徐诗富艳,李多用事。李谓徐曰:‘公诗如女,善调脂弄粉’。徐曰:‘公诗乃鬻冥器,但垜叠死人耳。’”[90]李九皋讽刺徐雅中诗“善调脂弄粉”,即是从辞藻上批评徐雅中诗过于富艳。不仅是文学,在宋代艺术领域的批评中,富艳也同样具此义指,如米芾评黄筌花卉画云:“黄筌惟莲差胜,虽富艳,皆俗。”[91]此即指莲花的形态和色彩。元明清至今,富艳在词采和风格上的意义已基本固化,说到富艳一词,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这方面的义指。比如刘壎评杜甫诗云:“或以豪壮,或以矩丽,或以雅健,或以活动,或以重大,或以涵蓄,或以富艳,皆可为万世格范者。”[92]这明显是把富艳视为少陵诗歌风格之一体。方回《瀛奎律髓》评诗,数处用到富艳一词,也主要是指诗的风格或词采,如评范成大诗云:“予选诗不甚喜富贵功名人,诗亦不甚喜诗之富艳华腴者。”[93]此即就诗的风格而言之。又如张溥说谢灵运“诗冠江左,世推富艳,以予观之,吐言天拔,政繇素心独绝耳”[94],显然也没有注意到谢诗富艳的真正内涵,只是从词采的浓重来理解它。再如四库馆臣说李来泰“制艺才藻富艳”[95]、《清文献通考》说王九龄诗“富艳”[96],其义所指,也概不出乎词采与风格。
富艳淡出史学批评及在文学批评中原始义指偏移,一方面是与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对词义的选择性注意有关。首先,早期一些既用于史学又用于文学批评的概念,因其重在文章写作的描述,在文史分途的过程中就易为文学批评所选择,于是就逐渐淡出了史学批评。其次,因富艳之艳是专指文章词采,义指具体可感,且在文学批评活动中被广泛运用,易为流俗所从,于是就成为后人的选择性注意所在,从而偏移了富的原始义指,只是简单地把它视为艳前面一个表程度的副词,消解了二者之间的并列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其义渺焉难详,后来论家不知它是从孔子所论“儒行”中移植过来的概念。《礼记·儒行》云:“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礼记正义》释云:“儒以多学文章技艺为富,不求财积以利其身也。”[97]“文章技艺”即指文章的写作能力。说明学习掌握了很多文章技艺乃是儒者富的一个标志,所以富就是非凡写作能力的代名词。至此也就可以明白,那时人们用富艳来赅括史家和文学家写作水平达到的这种高度,其实就是从“儒行”中引入的概念。由于富是对儒者知识文化素质的最高要求,本身即有其圣神性和崇高性,所以一旦引入史学和文学批评中,被奉为一种文章写作能力的最高体现和最高标准,专用于评史学和文学大家,也就是必然。左丘明、陈寿、曹植、谢灵运就是论者用“儒行”的标准评定出的能够矗立于儒者君子之林的史学和文学大家。从现存文献来看,这些作家曾经也确实以此来要求自己,曹植就是其中的代表,《前录自序》对“君子之作”所树立的那些写作标准,其实就是一种“多文”的标准,说明其创作是以“多文以为富”来要求自己,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儒者君子。而人们对其创作的认可,也同样是从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萧绎说他“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王通也说:“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98]肯定的就是曹植的创作合乎儒者君子之文的标准,以此成为砥砺儒行的士子心目中的文学大家。遗憾的是,后来一些学者不知富艳是从“儒行”中引入的概念,也就忽视了其所包蕴的深广博大的批评内涵,一般性地将其解为辞藻美盛之义。毫无疑问,由于对富艳词采、风格意义上的观念固化已久,也就造成今天对其早期原始含义的陌生,不能很好地认识左丘明、陈寿、曹植、谢灵运作品富艳的真正义指所在,仅仅是从风格和词采意义的层面对之进行认识。
注释
∨
[1][8]《华阳国志校注》,常璩撰,刘琳校注,第页,第页,巴蜀书社年版。
[2][3][45]《宋本春秋榖梁传注疏》,范宁注,杨士勋疏,第20页,第21页,第2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年版。
[4][11][14][17][22][36][42][52]房玄龄:《晋书》,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5][13]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十五,第页,第页,中国书店年影印。
[6][7]扬雄:《纂图分门类题五臣注扬子法言》,李轨、柳宗元注,宋咸、吴祕、司马光重注,《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第册,第页,第页,北京出版社年版。
[9]陈寿:《上三国志注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严可均辑,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10][15]魏收:《魏书》,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12][97]《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下册,阮元校刻,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影印。
[16][40][72][73]沈约:《宋书》,第页,第页,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18][23][39][43][54][55][56][57][58][7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页,第页,第92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19]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
[20]吉川忠夫:《解说——陈寿と谯周》,《正史三国志6》,陈寿撰,裴松之注,小南一郎译,第页,东京筑摩书房年版。
[21][24][48]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第页,第页,第44页,商务印书馆年版。
[25][86][88]刘昫:《旧唐书》,第3页,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26][35]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第—页,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27][29][34]陈寿:《三国志》,第页,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28][37][59][74][75][79][80][85]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年版。
[30]详见郭鹏《〈诗品〉曹植条疏证》,《唐山师范学院学报》年第3期。
[31][53]《金楼子校笺》,萧绎撰,许逸民校笺,第页,第—页,中华书局1年版。
[32]《说诗晬语笺注》,沈德潜著,王宏林笺注,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3年版。
[33]《曹集铨评》,曹植撰,丁晏纂,叶菊生校订,第页,文学古籍刊行社年版。
[38]沈德潜:《古诗源》,第页,中华书局7年版。
[41]白居易:《白居易诗选》,顾学颉校点,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44]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第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
[46]汪中:《左氏春秋释疑》,《清朝经世文正续编》第2册,贺长龄、盛康编,第页,广陵书社1年版。
[47]皮锡瑞:《皮锡瑞集》,吴仰湘校点,第页,岳麓书社2年版。
[49]《史通通释》,刘知己著,浦起龙释,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50][51]《廿二史札记校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60]姚思廉:《梁书》,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61][81][82][83][84]李延寿:《南史》,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62][63]萧子显:《南齐书》,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64]贺贻孙:《诗筏》,《清诗话续编》第1册,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65]姚范:《援鹑堂笔记》,《续修四库全书》第册,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年版。
[66]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朱德慈辑校,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67]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汪俊、黄进德点校,第页,广陵书社年版。
[68]李瀚:《蒙求集注》,徐子光补注,《丛书集成初编》第册,第91页,中华书局年版。
[69]详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3册,第页,中华书局年版;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第—页,甘肃教育出版社年版。
[70][71]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第页,第页,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
[77][78]《六臣注文选》,萧统编,李善、吕延济等注,第—页,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87]皮日休:《桃花赋(并序)》,《全唐文》,董诰等编,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8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90]朱胜非:《绀珠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第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版。
[91]米芾:《画史》,谷赟校注,第21页,山西教育出版社8年版。
[92]刘埙:《隐居通议》,《丛书集成初编》第册,第69页,中华书局年版。
[93]方回:《瀛奎律髓汇评》,李庆甲集评点校,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94]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殷孟伦注,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年版。
[9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4册,第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版。
[96]张廷玉等:《皇朝文献通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第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版。
[98]王通:《文中子中说》,阮逸注,秦跃宇点校,第26页,凤凰出版社7年版。
END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年第3期第-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上一篇文章: 果断收藏25种重大疾病定义思维导图超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