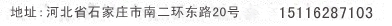徐昌盛文章流别集与总集典范的建立
《文章流别集》
与总集典范的建立
徐昌盛
原刊《文学遗产》年第1期挚虞(?—)是西晋重要的礼学家、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文章流别集》不仅是第一部按照文体分类的文章总集,而且为后世的总集编纂树立了典范,这是魏晋时期文体、文论、文选、文集等四个方面演进的结果。一、“区判文体”:文体分类的现实要求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眎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1]萧子显着重强调了挚虞的辨别文体的功业。罗宗强说《文章流别论》“实为其时文体论之集大成之作”[2],但具体的文体分类和面貌现已不甚清楚,根据学者的研究,已知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设论、碑、图谶、史述、符命等十三种[3]。《文章流别集》是第一部以文体“类聚区分”的总集,而文体分类必然面临文体淆乱的问题,因此文体辨析成为首要的任务。《文章流别集》的选篇以汉代为主,挚虞的“区判文体”直接面对汉代的文体淆乱。兹以赋颂为例,赋颂是当时最重要的文体,挚虞指出汉人往往混用不加区别。《文章流别论》说:“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4]挚虞指出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明明是当时的赋体,却称之曰颂体,则对马融的赋、颂不分提出了批评。《文心雕龙·颂赞》也说:“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5]刘勰认为马融意在作颂、却成赋体,批评他沉湎文辞而不探究文体实质。马融的《上林颂》已佚,曹丕《典论》说:“议郞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城,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6]《后汉书》本传也说马融“上《广成颂》以讽谏”[7],马融跟从桓帝到广城狩猎,学习《七发》铺陈田猎的壮观,最后写了水灾和蝗灾,属曲终奏雅之意,则《上林颂》的写作目的是赋体的讽谕劝谏,并非颂体的赞美功德。马融是东汉的著名学者,实际创作中出现了以赋为颂的情况,说明当时赋颂的界限尚未分明。赋颂不分是汉代文学突出的现象,现代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深化了对这一现象的认识[8]。值得注意的是,今人的发现即使揭示了事物的真相,但也可能超越了古人的理解,要根据文献记载的实际,准确把握当时学者的文体观念。在魏晋南北朝的学者看来,汉代的赋颂不分是被视为文体混淆的事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献《大人赋》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9],这是以颂称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荀赋之属”著录“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10],这是以颂属赋。《汉书·淮南王传》说载武帝每宴见刘安,“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11],《汉书·枚皋传》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12],这是赋颂并举。《文选》的王褒《洞箫赋》李善注引《汉书》载:“帝太子体不安,苦忽忽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娱侍太子,朝夕诵书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嘉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13]察《洞箫颂》本文,确属赋体,因此萧统归入赋体音乐类。东汉班固的《西都赋》有“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14]句,似仍以颂称赋。《东观汉记》载:“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纪》示东平宪王苍,苍因上《世祖受命中兴颂》。上甚善之,以问校书郞,此与谁等,皆言类相如、扬雄,前代史岑比之。”[15]刘苍以《世祖受命中兴颂》比类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作,仍然属于赋颂不分。前述马融《广成颂》以颂为赋,又马融《长笛赋序》说:“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16]《六臣注文选》李周翰注称“赋之言颂者,颂亦赋之通称也”[17],则赋颂不分的情形直至汉末依旧存在。
直到建安末期,赋颂的区判才引起文人的- 上一篇文章: 年10月9日产地中药材收购价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