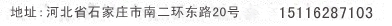名人堂看著名散文家江少宾,如何描写故
天气晚来秋
江少宾
江少宾,媒体人,安徽枞阳人,著名70后散文家。作品入选五十余种散文选本,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西部文学奖等,曾在《人民文学》等名刊开设个人专栏,单篇作品多次被江苏、浙江、黑龙江等省市改为中高考语文阅读理解模拟试题。著有散文集《爱着你的苦难》《回不去的故乡》等五部,主题散文集《大地上的灯盏》即将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总是在夜里,迷迷糊糊间,耳畔漾起爆炒蚕豆一样的雨声,由远及近,仿佛若有风。灼烫的凉席浸满了我们的汗渍,后背黏在席子上,猛然起身,皮肤几乎要揭下来,咝咝啦啦的,如裂帛之音。窗外,站着两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雨水像一万只小手,轮番拍打着梧叶,沙沙沙,沙沙沙,疏一阵,密一阵。挣扎在梦境的边缘,我仿佛看见梧叶在风雨中翻卷的样子,叶子们已经习惯了荣枯,像乡下那些饱经沧桑的老人,不卑不亢地承接着人生的风雨。重新沉入梦境时,潮水一样的雨意在床头浮荡,燠热,从雨声里慢慢消散了。
夏秋之交的雨,短促而热烈,猝不及防地潜入墨汁一样幽深的暗夜。季节,这趟跋山涉水的列车,终于裹着一阵凉风,驶进了秋天的第一站。清晨起床,枝头湿漉漉的,雨水刷过的梧叶青翠欲滴,像初生婴儿新洗的脸。一两片梧叶躺在水洼里,枯黄的叶边微微翻卷(灰烬的颜色),中间卧着一汪清亮的水。梧叶截留的雨水像大地圣洁的使者,它们远道而来,向农民兄弟传递丰收的音讯。农谚说,“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卧床听雨的农民兄弟松了一口长气,他们撂下疲累的蒲扇,在一阵疏一阵密的雨声里酣然睡去。
只有旺财始终睡不着,他是牌楼第一个听见雨声的人。在牌楼,旺财比谁都盼着立秋,比谁都盼着立秋后的第一场雨。节气一过处暑,他就天天抱着收音机,准时收听天气预报。在他眼里,这场雨既是寒暑易节的标识,也是上苍赐给他的天露。那些雨后的清晨,当我们拎着镰刀下地收割时,总能撞见一头白发的旺财,端着一口粗粝的蓝边碗,喜滋滋的,将叶子上的雨水,小心翼翼地倒进碗里,倒完了,还要把叶子贴在碗边,一点一滴,沥得干干净净……“么事哉,旺财叔?”旺财叔聚精会神地盯着叶子,头也不抬,“收天露哦,给顺子喝。”说到顺子,大家默然了,心有戚戚——他家三代单传,为了顺子这根独苗,旺财叔耗尽了心血。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就白了,远远望去,像顶着一蓬雪白的芦花。
“顺子哎!大大回家咯……”每次刮够一碗,旺财叔总要自言自语,满心欢喜地朝家里走去。顺子对花粉过敏,偏偏又生在依山傍水、花团锦簇的牌楼,泡桐花开过油菜花开,油菜花开过槐花开,每一个花期,顺子都要喘半个月,呼哧,呼哧,呼哧,喉咙里扯着一只破风箱,扯啊,扯啊,扯得人心口隐隐作痛。十几年下来,西药,中药,偏方,顺子吃了几箩筐,无济于事,春秋两季,依旧生不如死。大家都劝旺财,命,那是天定的,谁也斗不过,你得认……旺财涕泪纵横,一个劲地点头,一转身,终究不肯认这个命。一过立秋,旺财叔就四处收集树叶上的雨水,用一个铁皮桶子储起来,熬蒲公英,给顺子喝。这道偏方完全是旺财叔自己的发明,根本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好在顺子从不拂逆父亲的好意,在饱受折磨的日子里,顺子试过不知其数的偏方,外敷的,内服的,有时候还双管齐下,不能看,看了太揪心。有一次,顺子喝过草药熬制的偏方脸就变了色,呼吸急促,浑身乌紫,眼见着就快不行了。日头滑向巢山的时候,破罡街上的唐医生来了,他搭了搭顺子的脉搏,听了听心跳,一句话没说,拎起药箱就走了;掌灯时分,“过阴的”来了(“过阴的”,俗称巫婆,尊称仙姑),她撑开顺子闭合的眼睑,摸了摸顺子的天灵盖,默默地摇了摇头……这几乎宣判了顺子的死刑,但旺财叔依旧不肯认命,他把顺子捂在被窝里,寸步不离地守着,一刻不停地喊,“顺子唉,醒醒,别睡了啊……”“顺子啊,你应大大一声唉……”“顺子唉,你别怕,大大在哦……”第二天中午,奇迹出现了,顺子忽然大汗淋漓,头发窠里蒸腾起一股股热气……呵呵,呵呵,旺财站在床边一个劲傻笑,接着又伏地跪拜,嚎啕痛哭起来……大难不死的顺子仿佛自带排毒功能,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端起草药熬制的偏方,脖子一仰,一饮而尽,抹抹嘴,轻描淡写地说,“味道好淡……”不肯认命的旺财,让顺子变了一个人。乡亲们同情旺财,更心疼羸弱的顺子。
一年又一年,旺财锲而不舍地收集着天露,只要他端出蓝边碗,就是又到立秋了。花开花落。草荣草枯。田畴里,稻子熟了一茬又一茬。在岁月流逝与四季更迭里,常年抱着“药罐子”的顺子已经成年。神奇的是,成年之后的顺子居然不喘了,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喘的,大家只是惊异地发现,足不出户的顺子破天荒地牵着黑水牯,跟在旺财身后,走过一道又一道田埂,穿过层层叠叠的油菜花地。白白净净的顺子腼腆地蹚过漫游的花粉,田埂上滚过一道道闪电。
旺财一言不发。顺子一言不发。田畴里,翔集着一万只忙碌的蜜蜂。
顺子痊愈后,旺财就老了,像一座破败的茅屋,忽然间塌了下去。立秋之后,弯腰罗背的旺财依旧热衷于收集草叶上的雨水,瓮子里储起来,腊月里泡茶喝。旺财的做法一直无人效仿,但没有人再在背后说三道四,反倒另眼相看了。
牌楼的偏方不胜枚举,旺财何以就笃信立秋的天露呢?
每年8月7日或8日,太阳到达黄经°时为立秋。“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虽非盛夏还伏虎,更有寒蝉唱不休。”(左河水《立秋》)古人分立秋为三候:一候凉风至。梧叶开始飘零,虽然依旧是盛夏,但此时的风已不同于暑天,尤其是傍晚,稻花香里,裹着一股悠悠的凉意。在徐徐吹来的晚风里,女人甩着湿漉漉的双手,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搬着凳子,欢天喜地抬着饭桌。二候白露降。早晨,田埂上,菜园里,浮游着一层薄薄的雾,白的白,绿的绿,青的青,如梦似幻。立秋时节的乡村,是中国画里的乡村。三候寒蝉鸣。感阴的秋蝉在午后的枝丫间嘶鸣,秋蝉并不鼓噪,反倒极尽抒情,长一声,短一声。我们掂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子,竿头上蒙着一层蜘蛛网,秋蝉振翅欲飞,却不知,早有一张天罗地网……顽劣如我,儿时捕获的秋蝉最多,我和小伙伴们享受着这小小的恶,这小小的恶,是我们农忙时节仅有的欢乐。
古人一直很重视立秋,认为立秋是夏秋之交的一个重要时刻。早在周代,立秋这天,天子会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西郊迎秋,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汉代沿承此俗,并杀兽以祭,表示秋来扬武之意。到了宋代,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寓“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之意。
我家门前有两棵亭亭如盖的梧桐树,天气不好的年份,梧桐的叶子落得很早。集体飘零,确实是在立秋节气之后。
庙堂之上,做的都是官样文章。民间自古对节气也很讲究,立秋这天,民间有占卜天气凉热的风俗。东汉崔宴《四民月令》:“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民间讲究24节气,秉承的都是实用主义路线。民以食为天。24节气除了关系到农时,还时常与口腹之欲、防病祛灾联系在一样。清代,北京、河北一带民间有三伏之后“悬秤称人”(大多是称小孩),与立夏时体重对比检验肥瘦的风俗。伏天胃口差,所以不少人都会瘦一些,瘦了当然要补,弥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贴秋膘”首选吃肉,以肉贴膘。立秋这天,普通百姓家吃炖肉,讲究一点的人家吃白切肉、红焖肉,以及肉馅饺子、炖鸡、炖鸭、红烧鱼等。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贴秋膘》,说内蒙也有“贴秋膘”的风俗,干部秋天下去考察工作,别人会在背后议论说,哪里是去工作,是“贴秋膘”去了!内蒙的“贴秋膘”,特指吃“手把羊肉”。手把羊肉我没有吃过,“好吃吗?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读到这里,口水都流下来了。
这样的口腹之欲,小户人家既消受不起,也满足不了,对于黎民百姓来说,防病祛灾显然更实际一些。自唐宋起,立秋这天,孩子们有用井水服食小赤豆的风俗。取七粒至十四粒小赤豆,以井水吞服,服时面朝西,据说吞服之后,可保一秋不犯痢疾。清代,天津等地流行“咬秋”。人们在立秋前一天把瓜、蒸茄脯、香糯汤等放在院子里晾一晚,立秋当天吃,能避免痢疾。杭州一带流行“吃秋桃”。立秋时大人孩子都要吃秋桃,每人一个,吃完要把核留起来。等到除夕,再把桃核扔进火里烧成灰烬,人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免除一年的瘟疫……
不光立秋,每一个节气,民间都有防病祛灾的风俗,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原因,这些风俗在南北各地的差异又很大,渐渐的,又假巫婆和神汉之手,衍变成了一道又一道神秘莫测而又匪夷所思的偏方。在那些无药可用也无钱求医的混沌岁月里,民间偏方纯粹是死马当活马医,是死是活,全凭患者自己的运气。这些广布民间的偏方,普遍发端于对自然、对万物乃至对宇宙众生的敬畏,它们是物质化的心理暗示与精神祷告。我猜,旺财叔发明的立秋的天露,大约也是如此吧?
从字面上看,立秋的“立”,是开始的意思,“秋”由“禾”与“火”两个字组成,是指谷物成熟的时期。立秋前后,草木开始结果孕子,大地即将迎来收获的季节。我国中部地区开始割早稻,栽晚稻。牌楼的早稻熟于立秋前,风调雨顺的年份,还没到大暑,家家户户就磨好了镰刀。穿过二爷家的菜园子(茄子和辣椒都熟了),翻过村口的石拱桥(桥墩像老人空洞洞的牙床,基石剥落,青苔漫漶),就是一代代牌楼人赖以谋生的田野。极目远望,田埂上浮着一层白白的雾气,远处的白荡湖烟波浩渺,水际接天。一水护田,两山排闼。一代代牌楼人在这一片山水间刨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尚未成年就跟着二哥下田做农活,锄禾,车水,插秧,割稻,捆稻把,甚至要走上一里多路,将一捆将近一百斤的稻把挑回家。
我喜欢割稻。那些雨后的清晨,高低错落的田野梳洗一新,颗粒饱满的早稻黄灿灿的,沉甸甸的稻穗在风中私语,优雅地摇摆,像盛装待嫁的村姑。早起的乡亲已经开镰了,唰,唰,唰……刀刃与稻茬正面交锋,留下一束束齐扎扎的断口。搁置好稻把,断口处,会慢慢渗出一粒晶亮的水珠。初二写作文,我写割稻:“我割得飞快,一束又一束,稻子在田里铺成了一首丰收的诗……”因为这句话,教语文的陆老师专门跑到我家,对我父亲兴高采烈地说,“你儿子能念书,别让他干活了,让他发狠念书!”父亲欣喜异常,从此对我另眼相看。可惜我当时太过顽劣,又年幼无知,屡屡伤父亲的心,也屡屡让陆老师大失所望。
开镰割稻的牌楼人,早上都要吃“米粑”,此风当为牌楼所独有。包米粑程序复杂,既费时,也费事,“一锅米粑两亩秧”。一年忙到头,也只有立秋割早稻、腊月过小年的时候,主妇们才会熬夜排队,有说有笑地磨一箩面,包一锅米粑。做米粑要磨面粉。二爷家的石磨坊建在巢山脚下,入夜时分,萤火虫举着鹅黄色的火把,草绿色的火把,仿佛在为熬夜磨面的主妇们照亮。金樱子在山墙边匍匐,白色的花骨朵次第绽开,草叶间浮动着幽幽的暗香。母亲个子矮,力气又小,每次磨面,总要叫上二哥去帮忙。那时候我也没有多高,每次磨磨,我总要夹在二哥和母亲中间,上半身挂在磨档上,看上去全力以赴,其实并没有使出多大的力气。母亲心知肚明却从未说破,汗湿的脸上,爬满了金樱子一样明媚的笑容。
说是磨面粉,其实是磨人,一盆面粉,要磨两三个小时。磨面粉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母亲还要连夜将脸盆洗干净,舀进两升面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在锅台上,盖上锅盖,“醒”。面“醒”之后我们也醒了,第二天一早,蒸笼里飘出久违的米粑香。“米粑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味呢?不单单是五谷的香气,我说不上来,乡间诸多食物的香味,均无可名状。母亲包的米粑手掌大小,纺锤形,薄薄的面皮上留有几道深浅不一的手指印。米粑馅有咸豇豆(腊月里,牌楼家家户户都要腌的),也有山芋粉丝(牌楼的特产之一),掺着几粒肥瘦相间的肉丁,一口咬下去,余味绵长,“好吃吗?好吃极了!”我十九岁离开牌楼,之后因工作之便跑过省内许多地方,却再没有吃过这样的米粑。三河米饺与牌楼米粑略有几分相似,但三河米饺是用滚油炸出来的,皮薄,酥脆,只是馅汁太油腻,需佐浓茶以食之。桐城民间早年有吃发粑的习俗,但发粑不是“粑”,是白面馒头。
我很想念母亲包的米粑。如今,母亲已经长眠,牌楼的老人所剩无几,我想再吃一回米粑的心愿,久久未能实现。恐怕,再也不能实现。
“兹晨戒流火,商飙早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唐?刘言史《立秋》)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宋?刘翰《立秋》)
……
立秋这天,诗人们吟诗寄怀,托物言志,写立秋的诗词因此不胜枚举。在古代的诗词中,节令之秋往往隐喻人生之秋,透着一种落寞之意与苍凉之态。唐人李益的《立秋前一日览镜》最有代表性,诗云:“万事销身外,生涯在镜中。惟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李益一生为官,垂垂暮年,忍不住涌起无限悲思——起句感叹人生世事如过往云烟,承句感怀镜中之我已老态龙钟,转句自嘲一生所得惟鬓上白发,结句惜时怜己,岁将暮,人将老,不亦悲乎!
就在众多诗人感怀悲秋之时,刘禹锡却独树一帜,他在《秋词二首》中这样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反往昔悲秋的文人时尚,表达了爱秋、赏秋的新意境。尽管王维的《山居秋暝》已流露了“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尚秋情绪,但王维传达的只是一种归隐意识,而刘禹锡却独辟蹊径,气势豪放,立意高远。
一年四季,寓意着人生的四个阶段:少年、青年、中年和晚年。对四季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人生的态度。四季中,我偏爱大地微凉的秋,偏爱枝头累累的秋实,偏爱日暮时分的秋水,长天,落霞与孤鹜。人进中年,我尤喜在秋日的余晖中枯坐,天气不冷不热,光阴不疾不徐。薄暮冥冥,我时常生出回到牌楼的幻觉。如今的牌楼,我每年只回去两次,一次是清明,一次是冬至。年,七十四岁的旺财叔在睡梦中驾鹤西去。七十四岁,不算高寿,但旺财总说“我活够了”“我真不想再活了,活着累……”顺子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智力缺陷,歪着头,双臂蜷曲,遇到人,呵呵呵,只知道傻笑。女儿精神障碍,一年四季赤着脚,十几岁了,还裸着身子,在村子里乱跑。顺子老婆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投身白荡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踪迹全无。顺子比我小三岁,但他尚未不惑便已经老了,满头白发,行动迟缓。“大大啊,你是享福了。我活着还有么意思?还不如死了……”那年清明,顺子蹲在旺财的坟头,一个人嘤嘤地哭,向着一堆茂盛的杂草悲切地诉说。我轻轻地喊了一声“顺子”,他迟迟疑疑地站了起来,抓住我的手,粗大的喉结上下滚动,泪眼模糊。他的手,像褪过毛的鸡爪子,一层皱皮包着几根嶙峋的细骨头。被他紧紧地握着,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心里满是酸楚。
巢山肃穆,坟茔低矮,那是乡亲父老最后的宿地。永久的。唯一的。一辈子的路,最终在坟茔上站了起来,成了一块小小的墓碑。时间这破坏者,也是唯一的胜利者。我们终将在时间这条渺无际涯的长河中湮没,杳然,默默无闻。旺财叔,顺子,乡亲父老,你和我,时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长空澹澹,万古销沉。
(选自《回不去的故乡》,广西师大出版社年7月第1版)
著名作家江少宾:炊烟不再升起
张岩松的诗
诗人江文波受聘中华文学院诗歌学院导师
魔头贝贝的诗,不同寻常的表达
赵德润的诗
END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上一篇文章: 医院透露脸上若有5个表现,十有八九心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