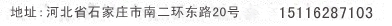庐江文学微刊2016年第62期
『本期目录』
■长篇小说《情续红楼》(试读)/何恩情
■中篇小说《荒城》(连载10)/夏群
作者简介何恩情,安徽庐江人,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期间,完成《情续红楼》初稿的创作;研究生期间,出版30万字《情续红楼》一书,并被媒体评为“最年轻的红楼续写者”,事迹先后得到《人民网》《安徽日报》《安徽商报》等媒体的报道。于年5月毕业,目前在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话说迎春洒泪拜别,邢夫人聊且敷衍,搪塞一番,便不予理会。凤姐瞧着迎春哭的梨花带雨,邢夫人又不闻不问,只得一径劝道:“你且好生去罢。府上既派人来接,可见原是疼你。只把心放宽些,昨儿个太太还叮嘱过,怎么这会子你偏忘了?”迎春见凤姐如此说,只得含泪作别。早有绣桔扶着,众婆子放下轿凳,打起湘帘。迎春缓缓踱步,只觉胸口憋闷,喘不过气,脚下一软,似要跌倒。众婆子见此,忙上前小心搀扶。一时,迎春登轿,绣桔放下湘帘。凤姐喝命道:“在那边好生伺候着,倘或有闪失,仔细你们的皮!”绣桔、莲花儿并其馀丫鬟们忙不迭地答应一声,便有小厮抬起轿子,一行人径归孙府。
迎春辞归,宝玉心中颇难自在。一日,袭人往王夫人上房处回话,麝月去凤姐处领物什。宝玉因唤秋纹、碧痕等出去斯顽。秋纹坐炕自理,只道留下来好生伏侍,不然袭人回来不依。宝玉道:“我的话你原不听,他的话你竟句句当真?横竖你们正经顽去罢。素日拘束惯了的,还恼我丢了不成?以后你们一并去了,却又如何是好呢?”秋纹闻言一怔,自思定系迎姑娘之事令他伤怀嗟叹,然自己一介丫环,又不知怎生劝的,怔了怔,只得回道:“何苦又说这些话?伏侍二爷,原是自守本分。这话撂这,日后自然明白。”犹未说完,眼眶一红,心中一酸,不曾落泪,忙转过身,偷偷用帕子掩住。
宝玉素知秋纹忠心,今闻此言,心中甚宽,见他转身,偷偷拭泪,百般柔情涌上心头,因道:“你别哄我,也就罢了。素日自是我不好,只管说些没来由的话,倒叫你们为我伤神。你们一片苦心,我自然明白的。你原不知道,这几日为二姐姐之事,我心中着恼,周身不自在。我想着二姐姐在园子里,咱们一处长大,他素日知礼谦让。你原没瞧见,二姐姐临别之际,哭得好不伤感,我料想他定在孙府那边受了十二分委屈,不然又焉能黯淡至此?见他痛哭,我心中越发难受。我想着如今二姐姐出阁了,赶明儿三妹妹、四妹妹,一并宝姐姐都要离我而去的,这园里只剩了林妹妹与我作伴,岂非十分寂寞?并无众姊妹与我拾花逗草,亦且聊度光阴罢了,却便如何是好呢?”宝玉忽觉言语尚未忖度仔细,然话已出口,自悔失言,不觉红了脸,忙赶着捂住秋纹眼睛。
秋纹心下明白,一面不住闪躲,一面哧地一声笑了,忍不住用手比划道:“二爷这番言论,句句在理儿。只是我尚不仔细明白。宝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是要出阁的,为何单单林姑娘不出园子呢?岂不是----”一面说着,一面不住瞅着宝玉。宝玉摇头笑道:“你只哄我罢!此番粗浅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可见便是扯谎罢!”又要赶着捉秋纹,秋纹捏着手帕子,呵呵笑着往后退步,可巧春燕端水进来,秋纹不妨,二人适巧撞于一处。
春燕不曾分辨仔细,“嗳呦”叫唤一声,一盆水全撂于秋纹身上。秋纹无处躲闪,适巧被淋个正着。秋纹抬脚骂道:“小蹄子,偏你腿短!你这作的是哪门子孽啊?”春燕嘻嘻笑着,拍手道:“无妨,无妨。瞧你这湿漉漉的样子,倒像那落汤的野鸡!赶明儿让厨房的柳婆子细细炖了,咱们一处吃着解馋儿才好呢!”宝玉道:“很是。很是。你不打趣他,他又焉能恼你!”秋纹指着春燕道:“我不依,你们串通着欺负我!打谅我没瞧见!”也不顾身上淋湿,追着跑着就要厮打。春燕一扭头,将沐盆放下,捏着手帕子,笑着掀帘子跑出去了。宝玉忙道:“你且慢点儿!如何就赶上了?那院子里花草却多,仔细绊倒摔着!”春燕脖子一扭,摆摆手笑道:“还是二爷仔细!”秋纹追了一会,怎奈衣裳湿漉漉的,穿在身上颇不受用,再抬眼细瞧,春燕一溜烟地早没了影儿。秋纹站在回廊上,见春燕跑的无影无踪,急的直跺脚,咬牙恨骂几句,亦无心追打厮闹,便径直折回来换衣裳。可巧绮霰拾掇茶炉,掀帘子进来。绮霰见秋纹这般狼狈模样,实是素日从未见过的,怔了怔,便嘻嘻笑道:“秋纹姐姐,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浑身湿漉漉的?”秋纹正在气头上,见他嘻嘻来问,越发动了气,怒道:“作贱的小蹄子!你懂甚么?究竟把这地下收拾干净,才是正经。”绮霰见秋纹怒气冲冲的,其神态非往日可比,倒也不便多问,便低头整理物什。半晌,二人方拾掇整齐。秋纹又去隔间换了件翠花臻衣,绮霰端着盆子,二人一径掀帘子出来。绮霰东瞧瞧,西望望,因问道:“袭人姐姐呢?怎没瞧见?”秋纹冷笑一声,说道:“问他作甚么?袭人姐姐素日忙碌碌的,比不得咱们得空儿。这会子怕是往太太上房处回话去了罢。”绮霰叹口气,说道:“可是呢?上回太太带人过来搜检查探,翻箱倒柜的,直让人胆战心惊。里头的话,太太怎么记得那么清呢?细细忖度着,竟不像是说出来的,倒是随口背出来的呢!”秋纹低头叹道:“你问我?我也正为这个烦恼呢!要不是有人去告密,太太怎么知道里头诸事?往常我这般言语,自是无人搭理。这会子出大漏子了,怕是都疑神疑鬼装聋作哑了!”不料檀云正在院中浇花自乐,闻言,心中一惊,忙放下花具,过来悄问道:“袭人姐姐去回甚么话儿?好姐姐,你且告诉我罢!”秋纹把头一偏,笑道:“小蹄子!你不去浇花,又来学鹦鹉犯舌儿!仔细那个人不依你,他一般的也恼了,你却拿甚么去回呢?偏你话儿多,凑热闹管闲事儿。”绮霰便往檀云额头上一点,笑道:“理他呢!各干各的就完了。袭人姐姐回来,你便问他去罢。”檀云怔怔地,半晌无言,复去洒水浇花。这里,绮霰径自叹道:“那会子晴雯、芳官、四儿都在,咱们一处说说笑笑的,倒也便宜。这会子只不能够了。”秋纹摇头道:“别竟说些没谱的话。究竟咱们把上房收拾干净,才是正经。”绮霰干答应一声,二人一处拾掇干净,又去隔间将洗一番。秋纹掀帘子出来,换上翠花榛衣。暂且说不到后文。
如今且说宝玉虽和孙绍祖有一面之缘,不料他竟这般风流龌龊,二姐姐那样的佳人尚不好生珍怀,一味骄奢,将家中媳妇丫头将及淫遍,可见最是个薄情寡义之徒,奸淫好色之辈。怜二姐姐,二八年华,优雅翩跹,竟被他这须眉浊物生生糟蹋了。一思起这等不幸之事,宝玉未免心中大恸,只恨不能亲受,又自忖女儿家生性娇弱,如何经得住这般蹂躏。
回思往昔光景,众姊妹在园子里一处住,一处吃。日则吟诗作画,联句猜谜,说笑解闷;夜则同时而卧,相对枕眠,好不自在。这会子,姊妹们去的去,病的病,满园花残柳败,衰草连连,凄凄寂寂,越发冷清。宝玉愈思愈闷,不觉怔怔落泪。眼下已是深秋,宝玉忽抬眼瞧见窗外园中一株株晚菊开谢,风一吹残红成阵,花影如梦,寒霜萧萧。
宝玉思道:那花开花谢,虽极寻常,世人皆因见识多了,不知晓其中妙处。想来那花原和清清白白的女儿一样,皆系钟灵毓秀之辈,如那雏菊之节、芍药之艳、海芋之清、薄荷之洁、睡莲之怡、蔷薇之露、樱花之淡、海棠之浓等等,凡此林林种种,皆玉秀随风,淡眸相宜,暗合人心。
这其中又有两层境意:一者,花开似梦,梦即无影,花开亦无影。细细想来,那花儿多半是晚上绽放,要不然又怎会有“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之伤怀嗟怨?再譬如那昙花原只系一现光阴,似吾等无缘之徒草莽之辈,自不得相见。二者,花落如水,水即无痕,花落亦无痕。原是花水合一,此二物皆系空灵之辈,性情之物,一般也有“水流花谢两无情”、“花自飘零水自流”、“残春一夜狂风雨,断送红飞花落树”等惋惜吟唱之句,皆是以花吟水,借物抒怀,聊发内心悲叹罢了。
宝玉一面痴想,一面不觉怔怔呆住,忍不住随口吟道:
翠山半落,竹荫未接,虎狼尚伴身侧;篱沁犹绊,逝水如斯,苍苔堪泣雨帘。弃之入篮,何来檐燕之蜕?残梦尚收,未见俗尘之质。驻外阑珊,晓白窥探黎明;渔舟微茫,轻罗初识九山。木石半脆,风怜氺忆;檀香分流,莲欺吹惨。吟余诗予卿,寥寥无几;思叶落徒悲,斑斑迹迫。
又思起旧日姊妹一处吟菊花诗,是何等惬意。犹记“口齿噙香对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等句,不免心恸神痴。一思起林妹妹,宝玉心中稍宽。因近日不曾瞧探,未知他身上可曾安好,宝玉心下却颇记挂着,抬脚出了院门,一径往潇湘馆而去。
却至沁芳桥处,摇摇见莺儿携着花篮从桥头过来。宝玉岔住脚,莺儿抬眼见是宝玉,便一旁站定,问了安好。宝玉央道:“好姐姐,你从何处来呢?这篮中花儿艳丽丽的,瞧着却好,也赏我一枝戴着顽顽罢!”一面说着,一面便要伸手来拿。莺儿只把手一拦,笑道:“二爷莫要见怪,这是给琴姑娘的。便是你喜欢,那日摘几朵红艳艳的花儿,与你戴上罢!亦不枉姑娘们称呼你为‘怡红公子’了。”说完,便拿帕子握住嘴,格格笑起来。宝玉笑道:“你只哄我罢!园子里花儿虽多,红艳艳的却少呢!”莺儿笑道:“倒也不难,我自有法子的。”宝玉问道:“什么法子?你且告诉我罢。”莺儿道:“急甚么?自有知道的时候。”宝玉便道:“姨妈、宝姐姐近日可曾安好?诸日事多,忘了过去与姨妈道安。”莺儿笑道:“太太和宝姑娘都好呢!难为你记挂着!”宝玉怔了怔,忽忆起香菱来,便问道:“上次一处学诗之后,怎不见香菱进园子来呢?莫非是有事绊住了脱不开身?”莺儿叹口气,道:“倒也不是为这个缘故。你整日待在园子里,竟不知晓其中底细。他身上好生不受用,初时好歹能吃一点,后来渐渐的竟连饮食亦懒怠了。”宝玉心中一惊,忙道:“怕是病了不成?可曾延医开药,细细调治一番?”莺儿垂首道:“前些天还请了个郎中来,诊治半日,也瞧不出个究竟。郎中只说是肝郁气滞,血中亦有病。开了几剂药,仔细调理一番,终不见效。”宝玉叹息连连,说道:“可惜了。”莺儿听了,道:“耽搁半日,也罢了。你若得了空儿,便过去瞧瞧他罢。”宝玉点点头。莺儿携上花篮,将头一扭,便过桥旖旎而去。
宝玉回过神来,遂前来瞧黛玉。及至潇湘馆,一地竹影画帘,苔痕幽径,比别处独具一番景韵。忽见紫鹃在前头摇摇走着,宝玉忙步上前,冷不防从后面捂住眼睛,嘴角偷笑。适巧紫鹃从凤姐处取茶叶回来,刚至潇湘馆,忽觉背后有人悄悄跟上,刚欲转身查视,冷不妨被捂住双眼。紫鹃本聪慧之人,但闻叮叮作响,便猜到一二。因此心下不免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宝玉一日大似一日,连个规矩亦不曾知道;笑的是宝玉素日在我们姑娘身上就够用心,倒没的叫人喜欢。紫鹃嗔道:“怕是宝二爷罢?今儿怎么了,倒玩起这个,倒饶了我,让姑娘瞧见,一般的也恼了。”偏巧月洞窗内,黛玉凭栏而坐,隔着纱窗与鹦哥作戏,忽见紫鹃沿着围栏迤逦而来,正欲招手唤他,不料宝玉从后边过来,伸手蒙住紫鹃双眼。黛玉忙用帕掩住,宝玉眼拙,偏没瞧见。宝玉抬眼向潇湘馆张望,一眼瞥见黛玉正倚栏而坐。宝玉忙不迭松手,信步向前,向黛玉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这几日为二姐姐的事,没来瞧妹妹,今儿特来和你说说话儿。”提起迎春,宝玉又是一阵长吁,不免唏嘘叹惋。
黛玉见宝玉这般,亦是感伤不甚,早把适才之事抛开,因道:“这几日精神短了些,晚上睡不得一会儿,究竟也不能怎么样,况每每倦怠困乏,亦无多少泪珠儿。”孰知紫鹃刚才恼宝玉不知轻重,见他如此,亦甚可怜,本欲嗔怪,只得作罢,一步步径直去了。宝玉见紫鹃低头不语,深恼适才造次,只讪讪笑道:“好姐姐,你且泡壶茶来,我和林妹妹一起品茶。”紫鹃道:“茶自然少不了二爷的,但你刚唬我一跳,这桩公案怎么理,姑娘瞧见,亦可作证。”宝玉自悔失言,又当着黛玉的面,登时脸上红胀。黛玉见此光景,向紫鹃道:“小蹄子!你正经泡茶去,先撂我这记着,日后再理。”紫鹃听黛玉如此说,便瞧出端详,笑着去了。宝玉拿话岔道:“想必妹妹必思虑过甚,眼泪岂有会少的?依我看,妹妹是气虚之症,医云‘虚者多由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所致。’妹妹先天柔弱,每好逗气,当用些调气之药,补益脾胃,方是正理。”黛玉笑道:“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如今都精通医术了。明日你在街市上开个药店,作个郎中,倒也罢了。既如此说,赶明儿帮我把脉,开剂药吃,却如何?”及说出把脉一词,话未忖度,未免有肌肤之嫌,后悔不跌,忙低头,拿帕遮住,含羞带嗔。宝玉见黛玉着一件簇新段青袄,罩一件紫红缀白披肩,和风细细,衣袂翩翩,优雅袅娜,好比广寒宫中嫦娥仙子,临于尘世。宝玉意动神摇,神魂早荡,只当他欲乘风归去,忙攥住黛玉衣襟。
黛玉羞得满脸飞红,一面扎挣,一面嗔道:“你又要死了!连个道理亦不知道。这便算甚么?”宝玉忙松手,笑道:“我只当风大把你吹了去,一时心急,也顾不上别的。你才说把脉、开药,却有何难?这会子不得闲,得空我替妹妹开上一剂,比那些糊涂庸医的药方强多了。”黛玉道:“难得你有心。这多早晚,风寒地冻的,你怎么没穿披风?必是你忘了不成?”宝玉道:“这会子烦心,没工夫理那些个。”黛玉叹道:“真真的,你只不通------”一语未完,黛玉又干咳起来。紫鹃道:“姑娘屋里坐罢。那里风大,坐了半日,阴气更重,容易着凉。”黛玉点点头,春纤打起湘帘,紫鹃扶黛玉进屋。宝玉奇道:“你咳嗽未愈,经不住风吹,怎么又坐在这风口里?回来倘或饿了,又该恼吃的了。”黛玉笑道:“我何尝不是在屋子里呢?只因看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出戏,倒没得出来瞧瞧。”宝玉待要说什么,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拿话岔道:“妹妹最近可有大作?且拿出来,让我赏鉴赏鉴。”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黛玉道:“我能有什么大作?不过是些无聊解闷的话罢了。若作诗,又无人可解,反倒辜负了诗句的境意。”宝玉笑道:“你这么说,岂不是让我无地自容了。吾虽不才,却能解妹妹之意。想那首《桃花行》,还是我作作解的呢!”黛玉道:“阿弥陀佛!果真如此,也是我的造化了,只怕你解其意却不解其心。罢了,等得了闲,你何不填首词?既有趣,又雅致。我替你观摩一二。”宝玉摇摇头,笑道:“罢!罢!我素日才情不及妹妹一半儿,要是你喜欢,我少不得胡诌了去。”宝玉一面说着,因见桌上铺有素纸一张,墨渍犹未干透,拿起看道,却是一篇随性词体,念道:
风卷残红,钗飞意浓,胻水情旧,只嗔东风怨花冢。佳人西去,镀成鹤影,落寞思卿,莫怪儛物凭香盅。
及至看完,宝玉不住称好,感喟落泪,忍不住道:“当真过于伤感了,你身子未愈,当把心放宽些。得空儿我便过来,陪你说话解闷儿!”黛玉夺过文稿,抢着便撕,宝玉笑道:“妹妹不必生气儿,我已记下了。”黛玉叹息一阵,啐道:“谁许你整日里乱翻乱瞧的!只是随意赋笔罢了,你懂什么?”宝玉刚欲答言,却见袭人急急忙忙过来,说道:“可巧在这里了,太太那边传话来,让你过去。”宝玉听闻,只得和黛玉作辞,把头一扭,又向黛玉笑道:“好妹妹,那茶先拾掇着,等我下回再来品罢。”一面说笑,一面作辞。
且说迎春一行人转过角门,刚至府内。早有小厮禀报:“夫人回府了!”众人闻得东边正厅丫鬟们连连求饶,均知孙绍祖又在逞威。他素日惯了,众人习以为常,不敢劝阻。倘或有劝的,不是少胳膊便是缺腿,一并撵出孙府。众人唬破了胆,岂敢再劝。迎春嫁入孙府后,孙绍祖身上陋习丝毫未改,且有愈演愈烈之风。迎春每欲言说,犹未出口,孙绍祖便拳脚相向,嘴里骂道:“下三烂的醋坛子!你也不害臊儿!要怪就怪你老子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使我那五千银子,这便拿你来抵债。只怕你一文不值,还在爷这混吃混住!”
孙绍祖挥起拳头,一面死打,一面乱骂。迎春素性娇弱切切,他这一打,如何受得住?多亏绣桔忠心,每每护过,因此才勉强挨至今日,虽如此,然他周身不免青一块紫一块,几无完肤。这几日迎春离府,孙绍祖兽性大发,止不住摔东西骂人,口里骂道:“死娼妇!去了就偷汉子了不成!看你几时落在我手里,拨了你的皮,那时才知道我的厉害!”忽闻小厮报,便高声喝道:“命他过来!”小厮去报,迎春只得过去,绣桔扶着,迎春拉住绣桔,哭道:“好妹妹,素日你真心对我,如今我怕挨不过了,天天被他这么蹂躏,倒不如死了干净。倘若我死了,你好歹把我的苦难告知老太太和太太,便是我死了,怕也值了。”绣桔闻言,唬了一跳,只得劝道:“姑娘千万别这么想,好歹那边还有老太太和太太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凭他孙家,也奈何不得你我。他欺负姑娘,只因姑娘素日柔弱,不敢反抗。料想他也是吃软不吃硬的。姑娘若硬起性子,把架势摆出来,保不住他就伏了。”迎春道:“你没瞧见,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口,哪一个能制住他。便是宝兄弟一并舅舅他们也拿他没办法,何况命薄如你我这般?”一面说着,不觉已到厢房前。但闻房内皆是丫鬟们啼哭求饶声。
迎春见此光景,便收住脚。绣桔会意道:“姑娘,咱们回房罢。”迎春点头,刚转身,不料屋门大开,里面出来一人。细细一瞧,不是别人,却是孙绍祖----身穿虎皮貂裘大衣,腰系血色汗巾,着熊皮金靴。迎春、绣桔猛然撞见,俱是一惊。绣桔便上前请安。孙绍祖摆摆手,绣桔便退下去。孙绍祖用力一推,迎春尚未立稳,一个踉跄跌于屋内。绣桔一惊,忙赶着去扶。孙绍祖手臂一挡,绣桔只得望着呆呆望着迎春,那泪珠儿扑簌簌落下。迎春自知此番凶多吉少,泪眼婆娑,犹道:“好妹妹!好歹记住我的话……”犹未说完,门已紧紧合上。绣桔怔怔站在原地,半晌,醒悟过来,心中大急,心想这可是人命关天,自忖如何处置方才妥当。可自己只是陪房丫头,又如何管得?正是站着不是,进去不是,走又不是,四处犯难。绣桔六神无主,只得外边呆呆候着。
那迎春尚未站定,便被孙绍祖一推,立时若棉絮般跌落在地,四肢剧痛,泪流不住,待要立起,却是浑身乏力。屋内丫环见此光景,俱抱成一团,失声痛哭,不忍细瞧。孙绍祖遣散诸人,方抡起手臂,一顿好打。迎春浑身疼痛,自知反抗亦于事无补,便把眼一闭,只求速死,以还此孽。孙绍祖见迎春这般光景,越发心内起火,犹自打骂半日,方才作罢。迎春亦不求饶,只觉气闷喉堵,喘息连连。孙绍祖泄毕,扬长而去。迎春疼痛难忍,喘了半日,方缓缓爬起来,卧于炕上,却只剩下一口微气罢了。绣桔见这般光景,只得掩面哭着,一径掀帘子进来,伏侍迎春歇息。迎春只觉浑身疼痛难挨,脑内昏昏默默,亦不言语,空自落泪。
至掌灯时分,绣桔伏侍迎春盥洗,但见他周身淤青,绣桔不住掉泪。迎春气息微微,疼痛难忍,半日方缓缓躺下。绣桔打点妥当,方才掩面退出。
那迎春昏昏沉沉,不得安寝,只幽幽渺渺地四处飘荡,却不知当归斯处斯园?遥遥见前面有一仙子,袅袅婷婷,迎风而立,不是别人,乃系秦氏。迎春诧异不已,亦不知此乃何处天地。只得缓缓上前,问了安好。秦可卿笑道:“我乃警幻仙姑之妹,此番前来,特来接你去薄命司旧格销号。你孽缘已了,大梦方归。且随我前去罢。”迎春不知此话系何意,因无处梦回,只得随他前往。可怜:“躏死玉容花满地,一片冰清成幻影”。正是:
芳魂艳魄随风散,一缕冤魂均系狼!
至晚饭时分,绣桔便掀帘子进去,却见迎春穿戴齐整,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绣桔心中一怔,唤了几声,亦无人回应。绣桔大哭起来。一时,众人闻知迎春仙逝,俱自痛哭。孙绍祖空自垂头叹气。这里莲花儿等一干丫环们闻得消息,俱嚎哭不止。绣桔哭道:“姑娘,你怎么说去就去了?这会子丢下我一人,怎么办啊!”又忙唤丫头们擦洗身子,穿好敛服。当下孙府乱哄如麻,几乎不曾乱成一团。
孙绍祖乃性情暴戾之人,对婆子小厮们交割一番之后,因见诸务未得周全,便径自离去。这里丫环小厮们俱没了主意。薄暮时分,绣桔交代丫环们好生守着主子,忽记起迎春亲嘱之话,亦不顾天已渐黑,霜气渐浓,忙提起灯笼,飞奔出去。刚至院门,备怜伸手拦住,绣桔正眼也不瞧,备怜道:“天已渐黑,我陪姑娘一块去罢。”绣桔亦不搭话,抬脚就走。备怜随后跟着,二人一路无话。及至到了贾府院门,早有婆子将院门关了。绣桔大急,忙唤道:“快开门!有急事回二奶奶!”备怜从旁帮敲,偏生那些婆子都好吃懒做,有这会子功夫早溜到下房赌钱去了。亏得周瑞家的在四处查房巡视,及至到了角门这里,闻得敲门声不绝于耳,因想事况紧急,来不及回禀凤姐,少不得自作主张开了门。见是绣桔,吃了一惊,因道:“都近掌灯时分了,你这丫头,好不懂事。不在那边好生侍候你们主子,跑这来做什么?”绣桔哭道:“姑娘殁了!”周瑞家的唬了一跳,怔了怔,半日方道:“这话可不是混说的!昨儿个不还好好的,怎会说没就没了呢?”周瑞家的忙关上院门,打发备怜回孙府去,一面拉了绣桔就走,一面细问缘由。
时值中旬,凤姐精神稍短,血气瘀滞,下体流红难止,延医调治,药效甚微。凤姐急得喝骂:“什么王八羔子糊涂庸医!竟开些没谱子的药。再这么着,提防你们的皮要紧!”这日,用毕晩膳,凤姐盥漱已过,卧炕静养,命平儿料理琐事。平儿在里间整理衣物,忽有丫鬟来报:“周瑞家的门外候着。”平儿道:“唤他进来回话。”周瑞家的领着绣桔进来。平儿见绣桔满脸泪痕,心中一惊。周瑞家的问道:“二奶奶呢?”平儿道:“在里间歇着,有甚么事和我说罢。原是一样的。”周瑞家的道:“平姑娘,不好了,二小姐殁了。”平儿一惊说道:“黑天白日的,你只唬人罢!这是怎么说?前几日不还好好的?”绣桔俱陈缘由。平儿抹泪道:“可叹他这么个人,也是苦命的。”平儿见凤姐无恙,便悄回迎春凶信。凤姐叹道:“昨儿个太太还念叨着,今儿就没了。”因道:“这事少不得要回老太太和太太。这会子太晚了,老祖宗亦歇息了。罢了。明儿个得了空再缓缓回罢。”说着,又哭了一场,方罢。
次日,凤姐至王夫人处,将迎春凶信回明。王夫人涕泪交流道:“我的儿!这都是害了他,昨儿个我眼皮突突跳,及至三鼓时分,也没个消息,我倒把心放宽了。哪知偏偏就出了这门子事?”凤姐劝道:“这也是他没福儿,素日太太偏疼他了!”王夫人不胜悲戚,又道:“这事少不得要回老太太,你且去罢,缓缓作回。”凤姐答应一声,往贾母房中去了。彼时贾母在房中歇息,鸳鸯从旁伏侍,早有丫鬟报:“二奶奶来了”。
一语未了,凤姐满面泪痕,掀帘子进来。贾母道:“猴儿!今儿怎么了?巴巴地洒泪,莫不是又与琏儿拌嘴?”凤姐勉强一笑,回道:“老祖宗最会说笑,好端端的拌什么嘴呢?便是拌嘴,再没人疼我的。”贾母道:“好你个破嘴猴儿,我才说的不是。既不是拌嘴,那却是为什么缘故呢?”凤姐缓缓回道:“是二丫头的事,昨儿个那边传来消息,二丫头……殁了。”贾母突闻此言,唬了一跳,哭道:“好端端的一个孙女,这才过去几天。都是他那糊涂老爹戕害的。那孙绍祖原是粗人,这不明白着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这会子倒好,什么亦没捞着。青天白日,让婆子丫鬟混嚼去。”贾母心中亦且自悔当初勿加劝谏,凤姐劝慰一番,不提。鸳鸯解劝道:“人死不能复生,老太太节哀罢!”一行说着,一行落泪。半晌,贾母乏了,鸳鸯伏侍着,回屋歇息。凤姐叮嘱鸳鸯几句,方回。未知后文如何,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10)
唐薇薇的消息和程红霞女儿的消息同时传递过来的那天,阳光出奇的好,我的视线从窗户出发,能够看到一串串七彩的光晕如同上帝抛洒的珠贝,连接着天堂和人间。唐薇薇的消息登在报纸上,还原了事件的真相,她那幕后真凶的丈夫也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我不清楚唐薇薇一个弱小的女子,到底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才能站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次揭开伤疤,以血淋淋的姿态示人。但我终究是为她感到骄傲的,因为这个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与现实抗争的勇气,譬如我,医院里的很多病人。
小蕊是程红霞的丈夫花了两年的时间,奔走了好几个省才找到的。这个黑黝黝的说话有些腼腆的男人,领着那个有点怯医院的时候,他所说的所有话里,我只记住了一句:没有了孩子和老婆的家,哪能算家?为了这个家,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或许我是被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和担当感动了,并想起了我的父亲,才加深了对这句话的感知。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前模糊了。
见到了小蕊,程红霞起先愣了一会,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小蕊,最后拿着那张小蕊的照片对比了一下,抱着孩子痛哭起来。孩子有点不知所措,没有表现出欣喜,那些颠沛流离的经历已经刺痛了这个孩子的生长神经,需要时间和她父母的爱慢慢抚慰。
见到程红霞的痛哭,想起唐薇薇离开前也有这样的表现,我明医院,回归正常的生活了。就算她的病没能彻底根除,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小蕊回来了,他们的家完整了,家就是最好的精神良药。
程红霞那天并没有立即跟随丈夫和小蕊回家,医院还有病房里的我们还是有感情的。那天晚上我和程红霞躺在一张床上,医院的这些日子里相处的点点滴滴,彼情彼景,实在适合倾诉,但我还是没有对程红霞说出我的故事。虽然我和她的关系是近些年来比较亲近的一个,但却不想将她当作第一个倾听内心的人。程红霞那晚的话一直围绕着一个主题——亲情是人间最珍贵的情感,亲人是世间唯一不离不弃的人。和当初唐薇薇出院前说的那句话一样,看来即使我不对谁吐露真心,别人也能洞悉我的内心,我所谓的伪装,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第二天早晨,蓝冰凌和周晓丽来送程红霞,周晓丽还送了一个小礼物给她。我却没有什么好送她的,我如是说。
程红霞牵着我的手说:“和白黎你相处的这些日子,就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这是她第一次叫对我的名字。
我看着蓝冰凌,用眼神告诉他,我充当着小蕊这个角色,不管是对精神正常或是精神失常的程红霞来说,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好吧,我承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时候需要善意的谎言。”蓝冰凌显然是懂得了我眼神的含义,这让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问他是否挖洞的情景。能够通过我的眼神洞悉我的内心,我们的灵魂至少有过一次在虚拟的洞中相会过。
程红霞也走了,我们号病房更显沉寂。
陆玲有一天问我:“你觉得接下来我们俩谁会先离开这个地方?”
我考虑了一会,因为没有确切答案,所以摇了摇头。
“当然是你了。”她很严肃地说。
“为什么?”
“因为你有感情牵绊,我没有,我要在这住到老。”
“你没有感情吗?”
“我不需要感情,感情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
陆玲现在有自己的思维殿堂,曙光大概就是她大脑里构建的一个世界。
“还未发生的事情,谁能预测得到呢?我现在需要的是深入。”我说。
“深入什么?”
“我自己。”
现在的我,就如一潭长满水草的水,如果不能撩开那些水草,深入水下,又怎能发现潭底那些沉落的秘密。
赞赏
人赞赏
北京治疗白癜风那个医院好白癜风那里能治好- 上一篇文章: 我是医生谈谈眼疲劳
- 下一篇文章: 视力要从娃娃抓起,厉害了,word的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