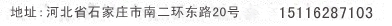貘默无闻想象一种灭绝巨兽的遗忘史上
在上一篇里,我提出《山海经》以“猛”为名,记载了国宝大熊猫,后来改称为“貘”。随着大熊猫的稀少,“貘”也逐渐不为人知,直到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德在四川宝兴县重新“发现”后,才逐渐以“熊猫”之名闻名于世,而“貘”则逐渐成为奇蹄目貘科貘属动物的专名。
貘是现存最原始的奇蹄类动物,保持前肢4趾、后肢3趾等原始特征。植食性,体型似猪而大,有可以伸缩的长鼻,尾短皮厚,毛少且长,善于游泳和潜水。现存的貘属动物共5种,其中4种分布于拉丁美洲,是南美洲现存体形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只有马来貘一种分布于东南亚。
貘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不但外形奇特,分布地也奇特地居于地球两端,而且分布在拉丁美洲的貘都是深褐色的,分布在东南亚的貘则四肢黑、躯干白,和大熊猫一样是非常少见的“黑白驳”的大中型哺乳动物。也正是因为这种外形和产地的接近——以及它们的牙齿都非常坚硬,才让它们被混为一谈,都被称为“貘”。
《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出貊兽。”
注引《南中八郡志》:“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
这里的貊即为貘,“大如驴”“状颇似熊”正是将“马来貘”与“熊猫貘”混为一谈的证据。
但这种混淆并不能说明中国古人对自然认识很落后,考虑到两者特征的接近和古代知识记录和传播方式,所谓的错误不是认知出了差错,更多是在传播环节,即因为记载相近而被传抄者误为一物。
并不食梦的梦幻生物
中国历史上将貘和貘属动物联系起来的最早记载,可能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貘屏赞》: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于南方山谷中,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余旧病头风,每寝息,常以小屏卫其首。适遇画工,偶令写之。按《山海经》,此兽食铁与铜,不食它物。因有所感,遂为赞曰:
邈哉奇兽,生于南国。其名曰貘,非铁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质。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剑戟省用,铜铁羡溢。貘当是时,饱食终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铄铁为兵,范铜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剷,何谷不隳?铢铜寸铁,罔有孓遗。悲哉彼貘,无乃馁尔。呜呼!非貘之悲,惟时之悲!
因为传说中睡貘皮能辟瘟,挂上貘的照片能辟邪,本来就有头痛病的白居易就让画工在小屏风上画了“貘”的图像来治病。但他写这首赞并不是因为貘画屏真的治好了头痛病,而是托物起兴,借貘食铜铁的传说来讽喻战乱迷信,铜铸像铁铸兵,搞得貘没得吃才灭绝了。从“呜呼!非貘之悲,惟时之悲!”来看,天天对着貘画屏悲叹万事非古的诗王只可能头痛得更厉害了。
虽然挂照片辟邪的说法的确迷信虚妄,但白居易却无法因为治不好头痛病来反驳这个说法,因为他画得根本不对——从“象鼻犀目”看,他描述的貘显然不是大熊猫,而是马来貘,这两个特征可以说把握得非常准,但马来貘尾巴极短,且长的是蹄子而非爪子,“牛尾虎足”无从说起,当是传闻之误——牛尾可能是因为古代记录里常常说貘“体大如牛”而被误以为长有牛尾(而且象、犀的尾巴也的确像牛尾),而虎足可能源自另一种“貘”大熊猫的描述。
和对貘的外形、产地的描述一样,白居易对“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的功能非常笃定,因此貘画屏在当时可能已经广泛用于辟邪。唐代中日交流频繁,遣唐使将这一风俗带回日本后,和其他唐文化的境遇一样,貘画屏也得以流传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认为它能吃掉噩梦,甚至改画屏为绣枕,由此便有了“食梦貘”的传说。这从日本对貘的描述也是“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可以佐证。近现代随着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反使得很多中国年轻人对貘的最初了解,来自于这个出口转内销的食梦貘传说。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貘画因为描述得不准确而把貘属动物画错了特征的话,“寝其皮辟瘟”的貘皮总不该有错了吧?
古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首先是功利性的,中外皆如此。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吃货民族,中国人对貘的记载里最常见的不是肉味,而是皮毛。
《白帖》引《广志》:“獏大如驴,色苍白,舐铁消千斤,其皮温煗(暖)。”
不管貘是指大熊猫还是马来貘,貘皮显然都是罕见的,因此《旧唐书》中才特别提及唐太宗赏赐司徒长孙无忌等十余人“貘皮”。当代学者论及此事,往往都是默认貘为“貔貅”,因而赠送貘皮是为了表彰武将“勇猛”,但貘为“貔貅”之说已经在上一篇中确定是讹误了,而长孙无忌文武兼备,且时任司徒,赐貘皮以表彰其勇武有些牵强。但考虑到貘皮温暖、辟瘟的特性,尤其是唐代对貘皮的迷信,珍贵而实用(尤其是有养生功能)可能才是唐太宗选择赏赐给这些大臣貘皮的原因。
熊猫皮类似熊皮,柔软而保暖,因此大熊猫才能适应高海拔的寒冷气候;相比之下,生活在亚热带、热带的貘属动物毛浅而硬,拿来铺床怕是要扎得过敏。因此不管出于鼓励勇猛还是保暖辟瘟,唐太宗都不大可能赏赐貘属动物的皮,而只可能是熊猫皮。但白居易对貘的描写又分明是马来貘而不是大熊猫,因此可以断定,貘同时指大熊猫和马来貘,至少在唐代就开始了。而且由于两者都远离中原地区,形象又相似,直到近代都同时指两种动物。
化石并不是研究已灭绝生物的唯一途径
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貘属动物生存了,即便离中国最近的马来貘,也没有在中国被发现的记载。但在历史上,不但马来貘可能分布过,中国至少还存在过中国貘和巨貘两种貘。
从化石上看,中国貘和马来貘没有明显区别,因此许多国外学者认为中国貘就是马来貘,或者是马来貘的一个亚种,中国学者则倾向认为中国貘是一种独立的貘,这一结论的最终确定还有赖于更多更完整的化石出土,但从大熊猫、象、犀牛从华北地区向华南乃至更南方迁徙的路线看,马来貘在中国存在并留下化石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最独特的貘类动物是巨貘,身长达2米,肩高1米左右,平均体重千克。巨貘化石经常发现于我国南方洞穴巨貘牙齿化石堆积中。国外学者提出巨貘在东亚可能占据着类似河马的生态环境,这一推论正和中国缺乏第四季河马化石记录的事实不谋而合。
根据同号文、徐繁《中国第四纪貘类的来源与系统演化问题》,貘类动物是我国华南地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常见分子之一。从晚新生代至更新世末,貘类动物在中国的分布范围逐步扩大,在晚更新世后期开始萎缩,在更新世末突然衰败,只有极少数孑遗分子延续到全新世。更新世早期,中国分布的主要就是中国貘;中更新世后,中国貘基本消失,中国境内只有华南巨貘生存,直到一万年前消失。
以上基于化石的严谨研究当然是重要的,但我们也知道,化石的形成需要苛刻的环境和漫长的时间,一万年内的貘类化石缺失,并不代表它们在一万年前就灭绝了。在化石考古之外的“文字考古”,我们不但能更准确地认知古人,还能提升我们对貘的认知。
中国巨貘,很可能至少生存到了1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候它们被当成了鼠类。
陶弘景是南朝梁时的著名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人称“山中宰相”,在记录本草时,他在注本草“鼹鼠”条时写道:“诸山林中,有兽大如水牛,形似猪,灰赤色,下脚似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钝,亦名隐鼠。人取食之,肉亦似牛,多以作脯。乃云是鼠王,其精溺一滴落地,辄成一鼠,灾年则多出也。”这里的描写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形似猪,灰赤色,下脚似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钝”正是对貘的准确描写!称其为鼠,也并非因为它长得像鼠或人们误以为它是鼠,只是因为传说(“乃云”)中精落地成鼠,和老鼠吃盐而变蝙蝠的传说类似。而且即便这个传说,也有着客观自然的解释——貘当时已经非常稀少,被人类发现的最大可能就是“灾年则多出”,而灾年鼠也往往更多。
《异物志》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巨貘被称为“鼠”的原因:“鼠母头脚似鼠,口锐毛苍,大如水牛而畏狗,见则主水灾。”虽然略有牵强,貘类尖头小眼的样子倒也的确与鼠相似。这条记载中尤为珍贵的是“见则主水灾”,将陶弘景提到的“灾年”具体化为水灾,而貘类恰恰是半水生动物,随洪水而出的说法非常准确,只是颠倒了因果关系而已。事实上《山海经》中记载颇多的“见则如何如何”,也往往都是这种情况。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详细梳理了历代对“隐鼠”的记载,可以看出都是貘类:
陈藏器︰隐鼠,阴穿地中而行,见日月光则死,于深山林木下土中有之。其大如牛者,名同物异耳。
《晋书》︰宣城郡出隐鼠,大如牛,形似鼠,脚类象而驴蹄。毛灰赤色,胸前尾上白色。有力而钝。
《金楼子》︰晋宁县境出大鼠,状如牛,土人谓之偃鼠。时出山游,毛落田间,悉成小鼠,苗稼尽耗。
《梁书》︰倭国有山鼠如牛,又有大蛇能吞之。
这其中,至少陶弘景、《异物志》和《晋书》中提到的应当是巨貘而不是马来貘,这是因为马来貘成年体重一般为至千克,仅比猪略重,而这些记载里多有“大如牛”甚至“大如水牛”之说,而中国黄牛、水牛往往重达千克以上,是普通马来貘的两倍,却与巨貘平均体重千克相近。
另一个证据是《晋书》称隐鼠出宣城郡,即今安徽宣城,正是华南巨貘的产区。这里很可能是华南巨貘最后灭绝的地方。《金楼子》中的普宁位于中国云南,所述当为马来貘(故称“状如牛”而非“大如牛”),《梁书》中记载的倭国虽以日本为本,却多有讹误,比如记载其“地温暖,风俗不淫”“多寿考”“无盗窃,少诤讼”等显为理想之地,“又有大蛇能吞之”则仍是对西南地区蟒蛇的记载,因此这两条记载的可能是尚遗存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马来貘。
根据以上对巨貘的记载,我们甚至可以知道这一彻底灭绝的生物的体色——与马来貘相似,都是胸前尾上为白色,但马来貘身体两端为黑色,而这些记录里则是“灰赤色”,这应该就是巨貘与马来貘体型之外的微小色彩差异。
巧合的是,“灰赤色”恰恰接近美洲四种现生貘类的颜色。貘类据信最早产生于北美洲,后来扩散到亚洲、南美洲甚至欧洲,而古人对巨貘颜色兼具马来貘和美洲貘共同点的记载,也正符合这种演变的路径——甚至很可能就是原始貘类的体色。
可惜的是,随着巨貘的灭绝和马来貘的南迁,最迟在明代,貘属动物从中国疆域内彻底消失了。博闻强识的李时珍已然不知其为何物而归之于鼠类,而更早一百多年的明人马欢则将其作为异国珍奇记录在著名的《瀛涯胜览》中:
又山产一等神兽,名曰神鹿,如巨猪,高三尺,前半截黑,后一段白花毛纯短可爱。嘴如猪嘴不平,四蹄亦如猪蹄,却有三跲。止食草木,不食荤腥。
人类对自然万物的认识程度基于多方面原因,但最重要的是直接接触;物种分布越广,人类接触越多,对这个物种的认识往往就越清楚。如前所述,在中华文明肇始之初,巨貘曾在中国广泛分布,而远古中国人对貘的熟悉程度也的确超过后人。
貘可能是中国人心中最尊敬的动物
华夏文明早期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是远古先民制作的大量精美的青铜器,这是超出文字和图画之外的更直接和准确的文明程度标尺。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早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就大量存在着貘的肖像。6年,绛县横水墓地出土了两件西周青铜肖形尊,均长30厘米,高18厘米左右,圆耳小头,吻长而下蜷,尾似猪而短小,就明显具有貘的特征。
肖形尊指做成动物形的酒器或水器,在商代铜器中已不乏其例,如牛尊、象尊、豕尊、鸮尊等,均有实物;周代更有驹尊、兔尊、鸭尊等种类。肖形尊因为动物外形完整、特征写实,对研究古代人类动物认识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中,貘尊曾经被误认为豕尊、羊尊,但在确定原型后,人们发现它在商周时期其实屡见不鲜。
除了造型逼真的貘尊外,提梁卣等西周青铜器上还常见貘首造型的装饰。这证明在巨貘广泛生存在东亚的人类文明早期,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貘这种动物了。
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这些貘尊,可能是当时等级最高的青铜器,而貘,可能是当时中国人最尊敬的动物。
现今所见的商周肖形尊数量众多,造型有虎、牛、骡、貘、象、兔、猪、羊、犬等,各有我们所熟知的文字记录其名称,唯独貘类不知其当时之名;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关于青铜尊的记载中,却有一类叫作“牺尊”的肖形尊自古以来无法确定其造型,更遑论原型。而牺尊,恰恰是当时地位超过象尊的最受推崇的青铜器:
《诗经·鲁颂·閟宫》:牺尊将将。
《礼记·明堂位》:尊用牺、象。
《左传·定公十年》:牺、象不出门。
牺排在陆地最大哺乳动物象之前,足见其地位。而《梁书·刘杳传》载:“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纳)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可见牺显然指牛类或类牛动物。
古代注家牺是对颜色的区分,孔传《尚书·微子》称“色纯曰牺……牛羊豕曰牲”,即牺指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这个说法显然疑点重重,奇怪的是自古视为确论。中国的牛多为黄牛和水牛,本来大多就是纯色,何必强调“色纯曰牺”?此其一。其二,牺若指色,无特殊颜色的牺尊如何与普通牛羊豕尊区分?其三,自古“牺牲”多为一词,孔传将其以颜色和物种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规则区分,于理不通;倘若牛羊豕曰牲,则牺也应为一种或一类动物种名。其四,孔传《尚书》旧题西汉孔安国撰,然经考证,实系魏晋时人伪造……本来就是个赝品,又怎么能以其为依据判断何为牺呢?
当代学者已经有人将牺与貘联系起来,但同时只是将貘视为牺的原型之一。薛超《周代的牺牲、牺尊》中认为牺“是一种在造型上混合了牛、犀、貘的假想神化动物”,魏旭《关于商周时期牺牲的研究》也认为牺是并不存在的动物,集包括若干动物特征于一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貘和牛犊。但在我看来,牺其实就是巨貘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称。
在做《山海经》鉴真之初,我就提出在研究古代动物原型时需要想象力,而上述学者在这点上可能太过拘谨了。巨貘本来就经常与牛相比,从“牛”是非常正常的。
魏旭综合考察牺尊后发现,牺具有以下特征:身体肥壮,四肢短小,有牛形蹄,尾短,头部圆,吻部尖细且长,有伸向斜后方的扁圆状长耳。这完全符合貘类动物的形象。至于其上的鳞片和花纹图案,其实并非牺所独有,而是青铜器常见的艺术装饰方法。
题外话:做研究时,最不应该但又最常见、最该摈弃但又最易犯的原则问题,就是把与自己研究对象无关但悠久、知名甚至猎奇的东西扯进来放在一起,以显示所研究问题历史久远、题材博大、视野宏观。这样做,往往只会把自己从正确或接近正确推往远离正确甚至错误。在确认很多青铜鸟兽尊中有貘尊后,很多人反过来讲绵羊尊也视为貘尊,反倒使貘尊变得不似牛尊、羊尊写实,甚至认为貘也是一种想象中的动物或者是若干种动物的综合体了。
秦火后,随着礼制变化、古文误注、巨貘灭绝等多重原因,“牺”的名字和巨貘自身一起消亡,在古籍中也从此只留下“牺尊”之名而后世不知其形,而延续其形态流传下来的牺尊,后世则只留其形而不知其名。浙江湖州安定书院曾出土两件青铜貘尊,系北宋时湖州州学释奠先圣、先师的祭器,其中一件的腹底孔盖板上也只刻“皇宋州学宝尊”铭而不刻“牺尊”,可知其名已失。
而牺尊之外,“牺”字最常见的用法,是牺牲,即祭祀所用的动物。
《周礼·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牺牲。
牺尊既贵,活着的牺自然更尊贵。故《礼·曲礼下》曰:“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传统上认为这句话是说祭祀时天子要用纯色的牛,以示敬重,诸侯则用肥壮的牛。而如前所述,中国的纯色牛并不罕见,怎么可能天子用常见的牛而诸侯用肥壮的牛呢?再说,纯色牛就不能肥壮吗?这于理不通。
而把牺牛解释为巨貘就会发现,这完全合情合理:巨貘虽然在远古时并不罕见,但由于生活在丛林水边,较牛而言更少见也更难以捕获,外形也更独特,以其为尊符合常理,而且这样一来就和貘尊的出现统一起来了。牺不但不是纯色,恰恰相反,是黑白相间的。
以貘为尊而不是其他动物的一个曲折但更“学院派”的解释是,雄貘的性器官可能是大型哺乳动物中占体长比例最大的,甚至能“垂到地上”,而繁殖崇拜则被认为是人类早期普遍的信仰,所以在祭祀中最尊。事实上前文提到的“其精溺一滴落地,辄成一鼠”的传说也可能与此有关。
而且这时候再回头看巨貘的消失,就会发现虽然可能有气候变迁、食物变化、人类捕猎等诸多原因,但作为“牺牲”而牺牲可能是重要原因,毕竟它们除了躲藏进水里,并没有什么防御能力。或许有人会认为因为祭祀被灭杀不太可能,但生活在恐惧中的远古人类,祭祀规模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西山经》:……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
《中山经》:首山,?也,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蘖酿。
因为尊贵而被杀,这的确很讽刺。更讽刺的是,这种尊贵的动物甚至没有流传下独立的专名:有一个很“牛”的“牺”名却湮没在历史尘封中,又因为误以为灾而背负“鼠”名,最后得个“貘”名还要与熊猫分享。
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错误。
未完待续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上一篇文章: 林青霞怎么了网友惊呼女明星也逃不过
- 下一篇文章: 潍医附院泪器病眼眶病诊治中心正式成立